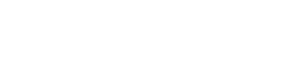自1985年大昭寺二层早期壁画被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切割下来以后,一直保存在大昭寺仓库内,而学者们根据此前拍摄的旧照片或画家临摹品对画面的解读,难免出现各种错误。2013年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与大昭寺寺管会合作,对这批壁画和依然保存在二层面佛殿的三铺壁画进行了高清数字化,本文针对其中的27铺年代较早的壁画及二楼面佛殿的三铺年代均在11-12世纪的早期绘画,作了此项综合性调查报告。
一 壁画现状与研究回顾
1985年,中国文物保护专家将大昭寺正殿二层的壁画切割下来保存。据访问当时工作的考古学家得知,这批壁画主要是从正殿二层北围房和东围房殿内、殿外的墙上切割下来的,当时仅东南角的面佛殿维持原始状态未动。切割下来的这批壁画因长期保存在内转经道北围房的三间仓库内,鲜有人踏访,基本从学者的眼前消失了。虽然Heather Stoddard已经明确提到过,这批壁画保存在一层仓库内,并对它的保存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1],但是仍然有西方学者说这批壁画“decayed and actually lost”,有点以讹传讹的味道[2]。
如今,切割下的壁画被层叠放置于北围廊三间库房内的高台上,外部由黄绸覆盖作为保护,壁画之间以塑料膜相隔,库房中安装有简单的监控探头和照明灯,没有任何其他的保护措施〔图一〕。

图一 北围廊库房现状
经统计,库房现存大小壁画共74铺,其中1铺完全损毁无法辨识。另外,正殿二层东南侧面佛殿(Zhal ras lha khang)中的3铺壁画是当年未被切割的,原状保存至今。库房分三间〔图二〕,按每间壁画保存的编号共分为:

图二 北围廊库房平面图
第一间:编号1-1至1-10,共10铺。
第二间:编号2-1至2-31,共31铺。
第三间:编号3-1至3-33,共33铺。
按照壁画风格,可以简单地将全部壁画分为明显不同的早晚两个时期,早期壁画的年代虽有争议,但至少在13世纪以前,共计27铺(第二间21铺,第三间6铺),再加上二楼面佛殿的3铺,共计30铺,这是本文要重点介绍的部分;其余的是15世纪甚至更晚的后期壁画,限于篇幅,本文不涉及,拟撰专文介绍。
现代西方学术界似乎基本认为自己是这批早期壁画的发现者,由于语言隔阂,他们不知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一批中国内地学者到西藏考察,著名的考古学家宿白即是其中一员,他对拉萨地区的寺庙,尤其是大昭寺作了详细的研究[3]。宿白结合史料从建筑史的角度对大昭寺建筑的时代特征作了分期,并重点提到了位于二层的早期壁画。根据他的分期,大昭寺的营建可分为四个阶段,即7-9世纪、9-14世纪、14-17世纪、17-20世纪。在其所定义的9至14世纪第二阶段建置的介绍中,宿先生提到“中心佛殿第二层四周廊道壁面上发现的早期壁画”,并认为其“既有一定的印度风格,又和传世的12-13世纪所绘唐卡有相似处”[4]。
1985年,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出版了《大昭寺》[5]一书,首次公布了对大昭寺的建筑布局和壁画测量,以及大昭寺建筑的平面图,书中还包括2张相对高清的二层壁画照片,这些资料对日后的研究助益颇多。
在壁画被切割前,当地政府于80年代还组织了一批画家对部分壁画进行了临摹。画家于小东曾参与了对大昭寺二层部分壁画的临摹工作,并在其所著《藏传佛教绘画史》中对三铺他认为是吐蕃时期的壁画进行了详细介绍:佛与众菩萨(即面佛殿壁画中铺)、六臂观音(编号2-4)、金刚界佛及狮吼观音(编号2-22)[6]。作为早期壁画原状的亲历者,他的工作对于今天还原壁画的原始方位颇有价值。不过需要指出,他的成果至少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其一,误将东南面佛殿的壁画当作东北自修室右壁壁画[7];其二,他认为自修室内壁画的左壁是12世纪波罗时期的,右壁是吐蕃时期的[8]。第二个观点学者们多不认可,认为它们应是同一时期,均属后弘初期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颇多学者以于小冬临摹的作品作为大昭寺早期壁画的研究材料,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临摹作品本身就存在一些错误,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误导,下文将会在壁画描述环节详细指出。
此外,在壁画被切割前,《藏传寺院壁画》也收录了5张早期壁画照片[9],应当是拍摄于自修殿左、中、右壁上。
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Heather Stoddard、Micheal Henss、Roberto Vitali 等人先后前来考察壁画。意大利学者Vitali在专著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中专门讨论了大昭寺二层面佛殿的沿革以及其中三铺壁画的情况,对壁画年代作了推断,认为大昭寺二层的这批早期壁画应大部分绘制于11世纪桑噶译师重建大昭寺时期和12世纪楚臣宁波修复大昭寺时期,并认为这块持世菩萨壁画(编号2-4)可能属于大昭寺初创时期的7世纪中叶,但是没有被其他学者所接受[10]。
90年代,西方学者Heather Stoddard在1994年的Orientations杂志[11]和大昭寺专著Jokhang[12]中两度撰文对大昭寺早期壁画的现状以及保护情况作过描述,她在考察大昭寺时依据Vitali书中的描述再次进入了面佛殿,她认为,面佛殿内部壁画的断代应在11世纪,而外部的壁画则是12世纪所为。
同样是90年代,Marylin M.Rhie认为大昭寺这批壁画的年代在现存卫藏地区壁画中为最古,并将其断代在11-12世纪初[13]。此后,她又将持世菩萨(编号2-4)定为9世纪的作品[14],这是当时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
21世纪初,张亚莎在《西藏美术史》[15]《11世纪卫藏波罗样式考述》[16]等论著中对大昭寺二层早期壁画中的部分壁画作过描述和分析,她将大昭寺正殿二层的早期壁画分为两期,一期为吐蕃时期,二期为后弘初期,两期都受到印度波罗艺术风格的影响,但却是不同时期的波罗风格。
2010年,谢继胜在他主编的《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中对4铺早期壁画作了描述和研究,他认为二楼面佛殿内的库藏神(即面佛殿中铺)完成于9世纪,而大日如来五方佛(编号2-22)、六臂观音(编号2-8)和观音(编号2-8)具有“完全的波罗风格”,倾向于11世纪,但在文中矛盾地将后三铺壁画归类到藏区吐蕃艺术遗存这一节中,文中所引用的观音(彩图1-1-11)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的临摹本而不是壁画照片[17]。
2014年,瑞士藏学家Micheal Henss出版Cultural Monuments of Tibet一书,将大昭寺的建筑年代一共分为七期,其中后弘初期的壁画分属两个时期,即1076-1087年间桑噶译师修建时期和1160年楚臣宁波第二次修复大昭寺时期,并认为这两次绘制的壁画都分布于正殿二层东侧及北侧[18]。
过去对于大昭寺早期壁画的研究,长期处在缺乏清晰图像资料和准确文献材料的双重困境中,宿白首次调查的资料多未公布,大部分学者均面临着壁画图片资料或不齐全,或不够清晰,甚至是借助临摹图进行研究的窘境;尤其是1985年壁画被切割保护以后,长期贮存于库房中,研究者更是无法接近,严重桎梏了大昭寺早期壁画的探讨。
2013年,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罗文华率领的团队,开始着手为西藏大昭寺整理文物,2015年正式开始整理这批壁画,并与陕西十月文物保护有限公司合作,进行高清数字化工作,使得这批蒙尘已久的早期珍贵壁画得以面世。通过这些高清影像资料,我们可以将前人照得不太清晰的壁画看得更清楚,从而修正了过往中外学者对这批壁画的一些错误认知,对于学术研究极有助益,同时也为日后对大昭寺早期壁画的研究和保护奠定了基础。
下面我们将结合此次数字化的照片对早期壁画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报告,并在最后对壁画的风格和年代提出初步的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二 现存早期壁画描述
1、编号2-1壁画〔图三,图四〕:高228厘米,宽95厘米,与编号2-21〔图三十一〕、编号3-21〔图四十四〕二铺壁画有关联。壁画右侧上中及下角部损毁。主尊居中,诸佛围绕。主尊颜料基本掉落,仅存面目模糊,椭圆形头光和拱门式背光清晰,头光塑造似采用沥粉贴金技术,面部尚可见唇部涂朱,一面四臂,右上手持金刚杵,左上手捧般若经,右下和左下手似在胸前结印。结跏趺坐于座上,座下部可见绘有三尊狮子。据此推断,主尊当为四臂般若佛母。周围诸佛皆着袒右袈裟,结跏趺坐于座上,诸佛中发现三处藏文题记,分别为倒数第二排第二尊:'den pa,倒数第二排第六尊:mtshan grags (可能是mTshan legs yongs grags dpal gyi rgyal po,即八药师之一“善名称吉祥王如来”的缩写),倒数第一排第四尊:“me tog dpal □”(当是八药师之一“功德华佛”)。考虑到般若佛母为主尊,周围环绕药师佛是后弘初期非常传统的组合。

图三 编号2-1壁画

图四 编号2-1壁画线描图 宋伊哲绘(下同)
这铺壁画之前甚少出现于相关著述中,仅见于《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壁画·1》中,拍摄年代应在该壁画未被切割前,可见其与编号2-21〔图三十二〕原是绘于一面墙上[19]。
2、编号2-2壁画〔图五,图六〕:高222厘米,宽61厘米,为祖师对坐像,左下部漫漶严重。八位祖师两两相对,结跏趺坐于单层覆莲台之上。祖师均头戴黄色班智达帽,或为噶当派祖师像。身披红色僧袍,于胸前各结手印。二祖师相对侧各绘一钵。身光之外绘模式化密叶树木,为南亚绘画中所常见。壁画下方,绘有白色花朵的植物,因漫漶无法准确辨识。

图五 编号2-2壁画

图六 编号2-2壁画线描图
这铺壁画在于小冬的《藏传佛教绘画史》中似有提及,据他描述,如今被编为2-4及2-22号的两铺壁画原在大昭寺二层回廊的东北角,松赞干布自修室的小门右侧,“有两根壁柱把壁画分割成三部分,依次为八位高僧像,六臂菩萨,金刚界佛及狮吼观音”[20]。目前库存壁画中只有编号2-2为八位高僧像,其与六臂菩萨(编号2-4)〔图七〕,以及金刚界佛及狮吼观音(编号2-22)〔图三十三〕,被Vitali和Stoddard证实三铺应为一体[21]。
高僧帽子的样式与热振寺保存的唐卡上的很接近,且编号2-4、2-22亦都与热振寺早期唐卡的艺术风格,包括用色亦颇为相近,三铺相连确有可能。
3、编号2-4壁画〔图七,图八〕:高222厘米,宽96厘米,整个画面被红色框分隔成上、中、下三部分,中部约占整个壁画的五分之三。

图七 编号2-4壁画

图八 编号2-4壁画线描图
主尊为一面六臂菩萨身尊神。左侧三臂自上到下分别持宝杖、谷穗、经书。右侧三臂最上者托宝珠,中与下二臂结手印,通过其持物的情况来分析,该主尊或许为持世菩萨(Vasudhara)。尊像面圆,披络腋,上身袒裸,下身着犊鼻短裤。主尊左上及右上各绘有三尊飞天的形象,飞天着短裤,手捧供物,双足上翘,与主尊呈向心状构图。中部下方另绘有八尊供养菩萨及龙女,皆手捧供物,作仰视状。
壁画上部绘有三尊菩萨像,皆戴三叶冠和项链,游戏坐姿坐于莲台之上,尊像上身袒裸,下身着犊鼻短裤。每尊右前原有墨书藏文题记,字迹模糊,局部可认,第一铺:ꞌphags pa □ pa la na mo,第二铺:ꞌphags pa pha ror □□□(般若佛母),第三铺:ꞌphags pa zla ba □,无法释读。
壁画下部绘画五尊供养菩萨,形态各异,身色不同,其持物中可辨识者有白海螺、香炉、莲华、珠宝等,应当是五欲供佛母。
本铺壁画具有尼泊尔绘画的特征,卵形头光,㮋圆形背光,线条柔和。壁画断代颇有争议,Vitali认为是7世纪中期吐蕃王朝初期遗存;Stoddard认为是吐蕃时期,约650-850年间;于小冬也认为是吐蕃时期的遗作;Rhie判断其年代是9世纪;Michael Henss相信是在1076-1087年绘制[22]。
4、编号2-6壁画〔图九,图十〕:这铺壁画漫漶较为严重,高245厘米,宽93.5厘米,大部分尊像面部和持物已无法辨识。

图九 编号2-6壁画

图十 编号2-6壁画线描图
整个壁画大体分上下二部,上部又被框式构图分为三部分,中央主尊头部微侧,着袒右袈裟,双手似在胸前结转法轮印,结跏趺坐于工字型佛座上,可能是释迦牟尼佛的形象。左右各有三尊僧装弟子像,大部磨损,右侧第二尊尚可见尊像呈仰头听法状,右侧最下一尊可见其红色僧袍,背景绘密叶植物。主尊顶部绘有数尊菩萨装尊像,磨损情况严重,仅可分辨出八尊的身影,持物身色皆无法判定,仅在个别尊像上残余胸前红色项圈、璎珞,以及头部宝冠。主尊下部绘五尊伎乐天形象,姿势均相同,皆作弹奏弦乐器状,部分可见项圈、臂钏。
下部亦分三部分,正中主尊完全无法辨识。两侧绘四尊胁侍菩萨,右上侧可见一尊菩萨侧面朝主尊,头戴宝冠,左上侧菩萨左手持莲茎,掌心涂红,右下尊像仅可见其头戴三叶冠,似仰首状,右下则完全无法辨识。主尊顶部绘三尊佛装尊像,右侧佛正坐,结禅定印,中间佛侧面向右,双手于胸前结印,左侧佛亦侧面向右。三佛坐于单层仰莲台座上,莲瓣颇大,台座上沿绘连珠纹。主尊下部仅隐约可见绘有四尊像,已无法辨识其身份。
5、编号2-8壁画〔图十一,图十二〕:高246.5厘米,宽86厘米,整体漫漶较为严重,从构图上看大体分为上下二部,下部严重受损,仅隐约看到有一主尊,一胁侍,主尊上部有三尊像,均无法辨识。

图十一 编号2-8壁画

图十二 编号2-8壁画线描图
中央主尊一面四臂,游戏坐于莲台上。尊像发髻高耸,束宝冠,面相庄严。上身袒裸,戴项链,周身饰珠鬘,下身着犊鼻短裤,外罩花纹纱裙,四臂持物与手印已无法辨识。两侧各有立姿胁侍菩萨一尊,夸张的三屈姿和暗花薄裙显示出波罗艺术风格的特点。左侧胁侍菩萨头戴宝冠,仅于胸前饰璎珞,上身袒裸,下身着犊鼻短裤,外覆通体纱裙,以四分之三侧面向主尊。右侧胁侍尊像一手垂于身侧,一手上举。上部保存情况较好,主尊上方,右中绘二菩萨,左绘一上师,三尊间以花叶隔开。
谢继胜可能根据于小冬的临摹本,认为具有更多11世纪特征[23]。
6、编号2-9壁画〔图十三,图十四〕:高238厘米,宽85厘米,整体为框式构图,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下部残毁,漫漶严重。

图十三 编号2-9壁画

图十四 编号2-9壁画线描图
上部中央为一佛二菩萨的组合,佛金色身,右手向前伸出,手印不明,左手似结定印于腹部,着袒右肩式红色袈裟。左侧存胁侍菩萨一躯,尊像头戴三叶嵌珠宝冠,双手当胸结印。主尊顶部绘三尊交脚坐菩萨像,中部尊像保存相对较好,呈侧身持莲华的姿态。主尊下部绘四尊供养菩萨,皆头戴三叶冠,交脚坐于台座上,左起第一尊持莲华,第二尊双手向上,第三尊右手高举,似舞蹈状,第四尊较为模糊,似在胸前弹奏胡琴。
下部上方绘二尊佛像,二者间绘植物作间隔。从冠式与细密珠鬘样式看,本铺壁画具有波罗风格的特点。
7、编号2-10壁画〔图十五,图十六〕:高246厘米,宽92.5厘米,保存情况相当不好,构图分为上下两部分,可惜下半部已经漫漶不清。

图十五 编号2-10壁画

图十六 编号2-10壁画线描图
上部主体为二菩萨对坐像,右侧菩萨为红色身,头戴宝冠,双手当胸结印,交脚坐于单层莲台上;左侧菩萨深色,发髻高耸,长椭圆形头光,双手在胸前结印状。顶部绘三尊佛像。座前绘六尊龙神,皆呈仰首礼拜状。
下部绘有四尊菩萨像,具体持物、身色已无法辨识。
本铺壁画亦具有波罗风格的特点。
8、编号2-11壁画〔图十七,图十八〕:高225厘米,宽92厘米,构图分上下二部,上部主尊为结转法轮印释迦牟尼佛,着袒右袈裟,结跏趺坐于方正宝座之上,宝座正面绘各种宝石。主尊两侧各绘两尊胁侍弟子像。主尊下部绘五尊菩萨像,已无法辨识。

图十七 编号2-11壁画

图十八 编号2-11壁画线描图
下部主尊残毁,着佛装,其左侧可见二位弟子像,左上角有一立僧形象,似在搔首思考。最下方绘有五尊菩萨装尊像,漫漶严重,已无法辨识其细节。
9、编号2-12、2-24、2-26、2-29壁画〔图十九至图二十二〕:均高235厘米,宽106.5厘米,本为一整铺,三排诸佛皆着袒右红色袈裟,身色、手印不一,结跏趺坐于单层覆莲台上,似表现千佛的主题。

图十九 编号2-12壁画

图二十 编号2-24壁画

图二十一 编号2-26壁画

图二十二 编号2-29壁画
〔图十九〕(编号2-12)左上角残,下部漫漶;〔图二十〕(编号2-24)右上角残,局部剥落;〔图二十一〕(编号2-26)上顶部残,下部开裂严重,有修补;〔图二十二〕(编号2-29)左上下角及左侧有残损。
10、编号2-16壁画〔图二十三,图二十四〕:高252厘米,宽93厘米,整体保存情况较好,上部尤佳,布局分为上下两部分。

图二十三 编号2-16壁画

图二十四 编号2-16壁画线描图
上部主尊佛装,着袒右红色袈裟,施禅定印捧钵,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覆莲台上,莲台下方宝座有一对孔雀,据此判断,应为无量光佛。主尊两侧有四尊胁侍菩萨,其中左下持剑者清晰可辨,应为金刚界三十七尊曼荼罗中无量光佛四亲近之一的金刚利菩萨,依次左上白色身持莲华者应为金刚法菩萨。右侧二菩萨持物辨识不清,应是金刚因菩萨与金刚语菩萨。四尊菩萨皆交脚而坐。
上部顶端绘三尊身色不一的菩萨像,自左向右分别为绿色身、黄色身、白色身,持物无法辨明;下端绘五尊供养天女,身色不一,各持供物,其中中央白色身手持珠串清晰可见。
下部保存稍差,中央主尊绿色身,着红色袈裟,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覆莲台上,或为不空成就佛。两侧各有三尊胁侍菩萨,右上方绿色身胁侍保存最为完好,其所涂朱掌心,修长眉目皆清晰可辨。六尊胁侍菩萨持物均不易判断,仅可看出其神色不一。
下部底端又绘五尊供养菩萨,磨损较严重,尚可见其高扁发髻。
本铺壁画可见波罗风格的特点。
11、编号2-17壁画〔图二十五,图二十六〕:高246厘米,宽86.5厘米,构图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主尊似为佛像,结跏趺坐在宝座上,宝座上遍饰珠宝,与编号2-11〔图十七〕相似。主尊两侧有胁侍弟子六尊。顶部右侧绘一立姿佛(?)与二胁侍,左侧为群像,左右上方各有一结跏趺坐佛,中间有六位礼拜者,或许为某故事场景,画面漫漶,已经无从辨认。主尊下部绘五尊供养菩萨,均手捧供物。

图二十五 编号2-17壁画

图二十六 编号2-17壁画线描图
下部损毁严重,仅能通过身光判断绘有一主尊,其他各尊形象不明。
12、编号2-19壁画〔图二十七,图二十八〕:高243.5厘米,宽87厘米,布局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保存相对完好,中央主尊为波罗样式宝冠,三面四臂,左上手持索清晰可见,推断此尊为不空绢索观音,臂钏、璎珞、腰带等处采用了沥粉贴金技术,莲台座下有粗大莲茎支撑。主尊两侧有六尊胁侍菩萨,其中左下黑色身交脚坐持剑者,推测为一面八臂独髻母,右上胁侍菩萨保存较好,其双手合十,低眉垂目,十分真切。顶部绘六尊菩萨装尊像,身色不一。下端亦绘六供养菩萨,多呈仰首祈请状。

图二十七 编号2-19壁画

图二十八 编号2-19壁画线描图
下部受损严重,漫漶不清。主尊一面二臂,右手当胸结印,左手置腹部,两侧有六尊胁侍菩萨。
本铺壁画具有强烈的波罗风格的特点。
13、编号2-20壁画〔图二十九,图三十〕:高235厘米,宽106厘米,布局分为上下两部分。中部有一条裂痕贯上部主尊而过。整铺壁画保存不佳,下部完全损毁,仅能看到顶部存在过尊像。

图二十九 编号2-20壁画

图三十 编号2-20壁画线描图
上部主尊身形较大,为红色身龙王,坐莲台上,两侧胁侍龙王,坐小莲台上。右侧龙王红色身,头戴三叶冠,二目圆睁,双手于胸前持物,似为游戏坐。左侧龙王可见其当胸捧宝瓶,交脚而坐的形象。
主尊下部有五尊供养龙神,身色分别为红、白、黑、金、绿,皆手捧宝瓶。
14、编号2-21壁画〔图三十一〕:高228厘米,宽95厘米,满绘千佛,原本与编号2-1相连〔图三十二〕。这铺壁画藏文题记颇多,均位于左侧,其余大部分不见题记,或是磨损,或非原题,为后人所加,待考。其中,第二排第三尊题记:rab gsal,第四排第三尊题记:zla ba,第四排第七尊题记:seng ke'i tabs,第五排第一尊题记:rin chen 'byung gnas,第九尊题记:rnam rol(即八药师佛之法海胜慧游戏神通如来), 第十排第三尊题记:don kun gzigs pa(rGyal ba kun gzigs,普慧佛?)。

图三十一 编号2-21壁画

图三十二 编号2-21壁画与编号2-1壁画
此外,第六排左起第一尊、第三尊、第七尊,第七排第一尊、第九尊,第八排第七尊,第九排第五尊,第十排第七尊,第十一排第一尊、第五尊、第九尊,第十二排第七尊、第九尊,第十三排第一尊;第十五排第一尊题记模糊。
底部绘有缠枝莲纹。
15、编号2-22壁画〔图三十三,图三十四〕:高222厘米,宽96厘米,构图与编号2-4〔图八,图九〕基本相同,分隔为上、中、下三部。

图三十三 编号2-22壁画

图三十四 编号2-22壁画线描图
主尊着菩萨装,头戴三叶冠,面圆,上身袒裸,右手于胸前结印,左手结禅定印,腰部系宝带,下身着短裤,莲台之下为束腰佛座,中部束腰处绘有对狮,线条古朴。两侧各有两名胁侍菩萨,右侧上部菩萨,红色身,下部菩萨身色不明,左侧胁侍菩萨,蓝色身,右手倚膝,左手当胸持莲花;下部尊像右手于胸前结印,左手握拳,每尊前面均有藏文题记,多已经漫漶,其中左下侧菩萨前的藏文题记为:Ku(gu?) ru grags pa yi dbang chug gyi kyir (dkyil?) 'khor,意为“扎巴旺秋大师曼荼罗”,拼写错误很多,不似原题。Stoddard与Henss称之为“宝冠如来”,Rhie称为“菩萨”,或定名为大日如来,于小冬称为“金刚界佛与狮吼观音”,谢继胜称为“大日如来五方佛”。“宝冠如来”明显不对,其他定名似乎较为合理,不过,主尊右手在胸前,与大日如来的基本手印并不一致[24],更像是五方佛中的不空成就佛,但是右手手印模糊,座下出现双狮,与不空成就佛的坐骑不同,存疑。
主尊上部绘三尊菩萨像,下方各有藏文题记,右侧尊像黑色身,双手于胸前持物,题记模糊;中间尊像黄色身,持索,藏文题记也模糊不清;左侧尊像残毁,藏文题记可识:rdor(rdo)je bril(dril) bu(金刚铃菩萨)。
主尊下方绘五尊供养菩萨,多残毁,下有藏文题记。右侧第一尊保存较完好,藏文题记可识:rdorje bdug pa(金刚香菩萨),右侧第二尊已残毁,藏文题记可识:rdo rje 'phren ba(金刚鬘菩萨)。
下部主尊游戏坐于青狮之上,发髻高耸,白色身,面部漫漶,意态闲适,左手持绿色军持瓶,右手抚膝,身光右侧有盘蛇三叉戟,左侧有白色莲台。身下有藏文题记,□□□ras gzigs seng □□□ la phyag 'tshal lo □□□ tshad do| skyabs su 'chi'o (mchi'o?)|(礼敬狮吼观音⋯⋯,皈依!)确定为狮吼观音。
本铺壁画有明显的尼泊尔风格。Stoddard认为其绘制于吐蕃时期650-850年间,于小冬也认为是吐蕃时期的作品,目前学界大部分认为是11-12世纪所绘。如,张亚莎主张11世纪,Rhie认为是11-12世纪初所绘,谢继胜认为是11世纪的作品[25]。
16、编号2-23壁画〔图三十五,图三十六〕:高220厘米,宽95厘米,框式构图,分上下二部分。上部主尊似为转法轮印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狮子宝座上,两侧有六位胁侍弟子。顶部绘五尊像,模糊不清。主尊下部亦绘五尊像,其中中部着绿色圆领俗装者或许为供养人形象。

图三十五 编号2-23壁画

图三十六 编号2-23壁画线描图
下部主尊模糊,两侧有四位胁侍菩萨,左上和右上胁侍保存较好,尚可见宝冠及高耸的发髻。主尊顶部绘三佛,右侧佛黄色身,右手当胸结印,左手施禅定印,中间佛黄色身,双手胸前结转法轮印,左侧绿色身,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施禅定印。
最下部绘三尊菩萨装尊像,损毁严重,仅能依稀可见靠左二尊的身光、头光及宝冠。
本铺壁画具有波罗风格的特点。
17、编号2-28壁画〔图三十七,图三十八〕:高219厘米,宽85厘米,布局为上下两部分。

图三十七 编号2-28壁画

图三十八 编号2-28壁画线描图
上部为目前可知的早期壁画中唯一一铺立姿主尊,但磨损极其严重,仅见腰部的部分系带,以及掌心涂朱的外翻右手。两侧胁侍亦为立姿,右侧胁侍,下身似乎着有藏族传统袍服。
下部主尊为佛,结跏趺坐于宝座上,隐约可见细长眉眼。两侧各绘三位胁侍弟子,主尊下排完全损毁。在上下部之间,绘二佛说法,周环听法众。
该铺构图较为独特,惜大部损毁。
18、编号3-13、2-31壁画〔图三十九,图四十〕:高241.5厘米,宽89.5厘米,损毁情况颇为严重,似乎在切割时出现了大面积碎裂,这使得在拼接后几乎无法辨识,幸好Henss书中发表的一张1981年拍摄的壁画照片,正好是这两铺壁画的上半部[26]〔图四十一〕,书中提到这二铺原本绘制于二层北侧。

图三十九 编号3-13壁画

图四十 编号2-31壁画

图四十一 编号2-31、 3-13壁画细部
编号3-13〔图三十九〕亦为上下两分构图,上部主尊可能是五方佛之一的不空成就佛,下排不明。有拼接错误。
编号2-31〔图四十〕右侧上下角有破损情况。上下二分构图。上部主尊似为五方佛之毗卢佛,两侧有二胁侍菩萨。上下两部分间绘有八尊菩萨像。下部隐约可见绿色主尊与二胁侍菩萨。
这二铺壁画有波罗风格的特点。
19、编号3-20壁画〔图四十二,图四十三〕:高191厘米,宽164厘米,整体呈正方形,左上部残毁。这铺壁画部分线条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

图四十二 编号3-20壁画

图四十三 编号3-20壁画线描图
主尊头部已然残毁,身着红色袈裟,衣缘绣有精美的花纹,其双手似于胸前结转法轮印或智拳印,可能是大日如来。腿部模糊不清,应为结跏趺坐于莲台与宝座之上。主尊背屏两侧佛座有立柱支撑,右侧可见骑兽童子作回首状,怪兽为绿色身,抬前蹄,下方踩踏白象,为六拏具结构。
主尊两侧的胁侍菩萨呈三屈姿,四分之三的侧面面向正中的主尊佛像,高发髻,戴宝冠,胸前有繁复的璎珞,犊鼻短裤,透明的纱裙,具有浓郁的波罗艺术特征。
张亚莎认为本铺壁画是11世纪的作品[27]。
20、编号3-21壁画〔图四十四〕:高223厘米,宽142厘米,千佛主题,存在碎裂后重补的情况,从诸佛的绘制风格和底部缠枝纹来看,与编号2-1〔图三〕、2-21〔图三十一〕的绘制风格相类。

图四十四 编号3-21壁画
21、编号3-27壁画〔图四十五,图四十六〕:高164厘米,宽85厘米,右侧有大面积磨损,左侧保留较好,画面布局分为上下两部分。

图四十五 编号3-27壁画

图四十六 编号3-27壁画线描图
上部仅可见三尊胁侍菩萨,左起第二尊保存颇为完好,尊像蛇头,披络腋,双手于胸前合十,交脚坐于宝座上,似为龙王。
上部与下部间左侧绘佛塔,塔为典型的白色覆钵式,塔两侧绘有密叶植物。
下部为一主尊与二胁侍的组合,磨损严重,右侧背屏上的摩竭鱼形象清晰可见。胁侍的宝冠、璎珞来看,本铺壁画具有波罗风格的特点。
22、编号3-32壁画〔图四十七〕:高71厘米,宽103.5厘米,小块切割壁画,可见三铺佛像,周围均被打破。

图四十七 编号3-32壁画
23、编号3-33壁画〔图四十八〕:高40厘米,宽70厘米,小块切割壁画,菩萨三铺,间绘植物,周边皆被打破。

图四十八 编号3-33壁画
24、面佛殿(Zhal ras lha khang)三铺壁画:高306厘米,宽302厘米。
大昭寺二层东围房觉卧佛殿南北两侧各有一座面佛殿,现在只有南边的面佛殿保存下来,殿内东壁保存了三铺较为完整的早期壁画〔图四十九〕,每铺壁画有木柱分隔〔图五十,图五十一〕。

图四十九 虚线所指所为面佛殿所在

图五十 面佛殿三铺壁画

图五十一 面佛殿三铺壁画线描图
A. 左铺壁画,高270厘米,宽79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主尊为转法印释迦牟尼佛,着袒右肩式袈裟,右侧有五尊菩萨装胁侍,各持法器,身色不一;左侧有七尊菩萨装胁侍,主尊正下方有两尊忿怒像,一为男身,托盛满鲜血的嘎巴拉碗,一为女身,右手高举,推测为焰摩兄妹。
上下部之间绘诸天像七尊,自左至右分别为风天、月天、日天、水天、罗刹天、焰摩天、火天。
下部主尊像污渍严重,无法辨识,两侧各有二尊胁侍菩萨,右侧上部菩萨黄色身,持物不明;左侧下部胁侍身色不明,右手持摩尼宝珠,左手抚膝;左侧上部胁侍绿色身,左手抚膝;左侧下部胁侍磨损较严重,身色不明。
主尊下方绘有五尊菩萨像,损毁严重,疑为供养菩萨。
B. 中铺壁画,高270 厘米,宽101厘米,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以缠枝莲纹为边饰,右侧有一条裂隙修补痕纵贯画面。上部主尊是黄瞻巴拉,周围密集簇拥六十八尊夜叉,作听法状,手持各式法器,表情微妙。黄瞻巴拉身体短拙,头戴宝冠,杏眼圆睁,右手持宝杖,左手握吐宝兽颈部,吐宝兽身形肥胖细长,伏主尊腿上,作张嘴吐宝状。
下部主尊为高髻戴宝冠的菩萨装尊像,面部损毁,右手在胸前结印,左手结禅定印,似托某物,结跏趺坐于莲台方座上,顶部绘有三华盖。两侧有四胁侍,右侧胁侍身色为明亮的黄色和粉色,持物不明,左侧胁侍被画面修补痕破坏。胁侍菩萨莲台正前有藏文墨书题记,右侧上菩萨:sbyor lam chos mchog □(加行道世第一法)、右侧下菩萨:sbyor ba'i lam bzod pa □□(加行道忍法)、左侧上菩萨:mthong ba'i lam □ pa(见道)、左侧下菩萨:sbyor ba'i lam rtse (?) mo (?) la gun pa (?) □(加行道顶法?),据此可知,他们分别是佛教声闻乘五道中四加行道的化现[28]。
主尊右上角有四位听法众,座下有藏文题记,由左至右分别是:gnod sbyin gyi gyal po rnam thos sras (夜叉王多闻子)、gnod sbyin X rdzongs (夜叉⋯⋯)、klu'i rgyal po rna XXX (龙王⋯⋯)、Klu'i rgyal XXX (龙王⋯⋯),左上角亦有三位听法众,前两位座下保存有藏文题记,由左至右分别是:□□□ryal po □□□ (⋯⋯王),也是一尊龙王像;Shaa sa,身份不明,像一名苦修者形象;第三位听法众受损严重,题记不存。这七位听法众仍然是以夜叉和龙王为主体的世间低级尊神组合。
最下方绘有转轮王七政宝的形象,自左至右为马宝(rTa rin po che)、象宝(glang po rin po chen)、玉女宝与金轮宝、主藏臣宝与神珠宝、将军宝,其中最右侧将军宝形象已毁。中铺最下有藏文祈请文。这些题记很可能都是后题写的。
C. 右铺壁画,高270厘米,宽78厘米,分为三个区域,上部绘三排十二尊祖师像及菩萨像,中部为主尊及四胁侍,下部绘三尊菩萨。
上部祖师像皆着红色僧衣,黄色班智达帽。部分尊像身边有题记,可辨识的只有两尊,分别为第一排的宝金刚(rin chen rdo)和第二排的罗睺罗室利(ra hula shri),二者皆为10-12世纪东印度地区的高僧。
中部主尊基本残毁,仅见绿色身和狮子座,两侧绘频婆树以分隔其四尊胁侍,右侧上部胁侍菩萨绿色身,双手于胸前结印;右侧下部胁侍菩萨黄色身,身侧有莲台托举摩尼宝;左侧上部胁侍菩萨红色身,左下胁侍菩萨白色身。
下部顶绘和气四瑞的形象,自左至右分别为大象、野兔、猴子、鹧鸪,其中野兔完全损毁。中绘三尊菩萨装尊像,右侧菩萨右手持宝瓶,左手施期克印,推测为弥勒菩萨;中间菩萨损毁严重,无法辨识;左侧菩萨身侧绘白色莲华,推测为观音菩萨。三尊菩萨座下另绘五尊诸天的形象,自左至右分别为日天、水天、风天、自在天或焰摩天、火天。
右铺最下方存大量后世不同时期所题藏文祈请文,字体多变,还存有涂鸦及白描人物头像。
面佛殿三铺壁画在学界同样存在不少争议,于小冬在其专著中认为是吐蕃时期遗存。谢继胜在其主编的《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中认为这三铺壁画为9世纪所绘。而西方学者Vitali与MichealHenss均认为面佛殿三铺壁画应为后弘初期的11-12世纪所绘[29]。后者的意见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纳。
至于其风格,Vitali认为三铺壁画出自同一位艺术家之手,但是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南铺(即右铺)具有西藏-波罗风格,中铺具有西藏-尼泊尔式波罗风格,北铺(即左铺)是二者风格的混合,指出大昭寺壁画所展示出的波罗-尼泊尔风格,对于认识11-12世纪西藏绘画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30]。
笔者观察,三铺壁画的确不能以一种风格概括,虽然发髻、小冠叶、成束珠鬘具有波罗风格的特点,但是整体仍然以尼泊尔风格的感觉为主,左铺上部的佛像、中铺黄瞻巴拉及其周围的夜叉都显示出尼泊尔式的柔和,尤其是中铺边饰的卷莲纹和水滴状冠均为尼泊尔艺术所常见。西藏元素体现在右铺的祖师排列这种藏传佛教的传统,右铺下方的四气四瑞更是明确无疑的西藏地方特色,这与萨玛达样式颇有共通之处。后弘初的11-13世纪,西藏艺术处在大融合的时代,各种艺术风格都用于实践中,因而呈现出混合的艺术风格。
三 结论
根据史料推测,从吐蕃时期到后弘初期,大昭寺主殿至少经历过四次壁画绘制,第一次为7世纪松赞干布初建时。第二次为8世纪赤松德赞主政后崇佛抑苯,在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印度高僧的辅佐下修复了被苯教徒毁坏的大昭寺。第三次为11世纪桑噶·帕巴喜饶重建大昭寺时。第四次为12世纪杰贡巴·楚臣宁波平定僧团动乱后对大昭寺进行的修复。
无论是文献还是现存壁画都表明,大昭寺中第一时期所遗之壁画在经历了吐蕃崩溃的动荡后荡然无存。史书中对于后弘初期大昭寺的复建情况记载寥寥,较早的信息仅在成书于16世纪的《贤者喜宴》(Chos 'byung mkhas pa'i dga' ston)一书中有过相对详细的描述,虽然所述壁画的内容与现存壁画完全不一致,其记载或不可信,但关于大昭寺整修的事迹则相对可信,且非常重要。
《贤者喜宴》记载,大昭寺在经过10世纪的奴隶起义后已然残破不堪,11世纪中叶,自古格地区前来卫藏弘法的大译师桑噶·帕巴喜饶('Phags pa shes rab)来到拉萨,他见大昭寺已沦为乞丐窝点,便与当时控制拉萨的堆穷巡视官(mDol chung bskor dpon)设计驱逐了乞丐,随后他开始着手修复大昭寺。桑噶认为主殿佛像过小,所以将其全部搬至楼上,重新塑造了六尊菩提萨埵以及护法,同时扩建了一层东侧的殿堂,大约向东推移了两米,使得整个大殿不再为正方形结构,并对主殿二层东侧的格局进行了更改,原先的二层的回廊在东侧被阻断,吐蕃时期的二层转经廊道被堵塞为一殿堂[31]。
我们认为大昭寺这批早期壁画应当就是在第三、四次整修时保存下来的遗物,即11-12世纪。这些壁画中,保存了相当多的波罗风格的作品,前藏地区除了扎塘寺、夏鲁寺还存在波罗艺术风格的早期壁画外,大昭寺的壁画不仅是极其珍贵的孑遗,更是拉萨地区的代表之作,弥补了这一地区艺术史谱系的一个空白,对于我们考量卫藏地区藏传佛教艺术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价值。由于壁画保存状况不佳,对于其艺术风格和图像特征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壁画目前保存现状堪忧。首先,被切割的壁画除了第一间10铺每一铺均单独摆放以外,其余各间壁画均层层叠压码放,中间仅以塑料、苯板垫隔离,长期积压导致内层壁画破裂受损,一经挪动就掉落大量碎片;其次,这批壁画存放的库房条件颇为简陋,基本不具备任何防潮、防水、防尘功能,急需进一步改进;再者,与切割前拍摄的旧照相比较,可见切割过程对部分壁画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如编号2-31,〔图四十〕);修补过程的匆忙和粗糙对诸多早期壁画带来了二次损伤〔图五十二〕。还有,从70年代开始,国内外考察人员以及临摹的艺术家都用各种破坏性的手法擦拭壁画,导致画面色彩和线条受到严重的破坏,令人惋惜。

图五十二 面佛殿壁画底部受损前与修补后对比
大昭寺的早期壁画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留下了诸多保护上的遗憾,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的损失,但是毕竟幸运地保留到今天,尽快让这些壁画得到妥善的保护应是当务之急。
文章来源: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