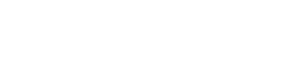站在9米多高的青铜和大理石雕塑《妈妈》(Maman,1999年)身下,产生一种被包围、缠绕、保护和压抑的复杂感受。当观众抬头望向母亲的躯体内部时,依稀可见的是几颗白色椭圆的卵状物,它们被高高抬起。母亲八条长长的、强壮的脚尖锐地刺向大地,强烈地传达出保护与拒绝的双重感受。

《妈妈》这件作品由于复杂情绪的感染力和对空间环境的另类诠释,开启了对“环境雕塑”的全新定义。这只巨大的蜘蛛从2000年英国泰特美术馆(Tate Modern)的涡轮机大厅开始,“爬”到世界众多著名艺术空间中,从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到苏黎世布克利广场。它既是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1911-2010年)一生对母亲强烈思念之情的倾述,也是她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命题——创伤、痛苦与感情的交织。
“蜘蛛是对我母亲的歌颂。它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母亲就像一只蜘蛛,她是一个纺织者。我的家族从事挂毯修补业务,我母亲管理着作坊。她像一只蜘蛛一样,非常聪明……蜘蛛保护着我们,一如我的母亲。”

在布尔乔亚漫长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无论是雕塑、纤维还是版画,都毫无掩饰地袒露着自己的秘密、创伤与痛苦。儿时她对父亲背叛的愤怒,对母亲忍气吞声的怜悯,成年后离开法国,对家乡的思念,这些情绪长期让她无法自洽,不得不借助艺术和弗洛伊德的学说自我疗愈、缓解痛苦。
在创伤、痛苦、愤怒的表达过程中,那件著名雕塑《小女孩》(Fillette)于1968年诞生,这是一个硅胶制作而成的巨大男性生殖器,以悬吊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无助感。1982年,布尔乔亚怀抱《小女孩》,面带神秘微笑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给她举办的回顾展拍摄了一张肖像。这张标志性的肖像自然成为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之中最具代言色彩的艺术作品。

20世纪80年代,很多艺术家还沉溺于非历史性的拼贴集锦,布尔乔亚的作品对创伤的表达已经暗示出后现代主义占主导性的情感结构。在哈尔·福斯特的分类中,早期后现代主义者们占有图像,而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想着占有真实之物。对痛苦和创伤的呈现成为布尔乔亚占有与回归现实的一种方式。
同一时期,另一位女性艺术家辛迪·舍曼也在向灾难图像的突显转变,展现出一些令人恐惧的女性生育和天生畸形的故事。母性的恐怖在辛迪·舍曼的作品中因为压抑变得古怪,令人厌恶的母亲身体成为卑贱之物的原始场所,这是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所定义的既非主体也非客体的一种存在范畴。那些充满着经血、粪便、死亡与腐烂的灾难场景,唤起的是一种极端状态。同样作为创伤表现的布尔乔亚的场景,则要干净许多,在此,创伤并未以卑贱的图像迈向形式消解,而是以净化的崇高堆铸成为痛苦的纪念碑。

在布尔乔亚的创作中,材料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从硬到软的奇特过程,无论是《父亲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Father,1974年)中的硅胶材料,还是在她艺术生涯最后15年开始逐渐增多的纤维材料,材料在重新处理艺术家与环境的关系过程中,产生了神奇的效果。麻布片、棉纺面料和铁丝的交缠,那种柔软又扎人的视觉与触觉上的感官特点经她处理,传达出内心的痛苦与试图和解的努力。
此时,纤维艺术也正在挣脱自身在材料领域的隶属地位和工艺束缚,从材料作为媒介语言跨越到渲染和表达内心隐秘之情的载体。波兰艺术家阿巴康诺维兹的《红色阿巴康》用强韧粗糙的剑麻编织出波浪运动,把纤维的艺术语言和本身蕴涵的强大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布尔乔亚则把布料经过缝纫、覆盖、缠裹等手段,与铁丝网等其他材料共同制作出《情侣》系列、《细胞》系列、《肖像》系列,她赋予这些作品以自传般的述说特征。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对话方式,从她生命中抽出最潜在的那根生命丝线,在创伤的废墟之中,织造出一座柔韧的生命之塔。

“永恒的丝线”是展览的主题,也同时构成了布尔乔亚在纤维艺术和软雕塑方面的成就。与博伊斯使用油脂和毛毡来疗愈战争创伤一样,布尔乔亚也用悬挂的布料与棉麻,用刺入和编织来疗愈最深层心理的愤怒、无力、恐惧和悲伤。她最后也许成功了,也许没有,无论结果如何,这些疗愈之作与那只高高盘踞的蜘蛛一起,都给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视觉和身体体验,以及最深切的情感共鸣。
文章来源:《艺术与设计》2月刊;
文:刘向娟Liu Xiangjuan
图:龙美术馆Long Muse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