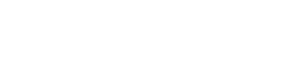日光是悄无声息地从沙发脚边撤走的,灯亮起。这已经不知是张晓刚在北京的第几个工作室。高大、宽广、庞杂,既能容纳巨幅的画布和装置,又能无处不张贴放置他收集的照片、图片、纪念品、CD、颜料、杂物……这是张晓刚喜欢的风格——杂乱而冗繁,反倒给人一种安全感。他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发呆。
1981年发表自己的第一张作品,迄今已经33年。这三十多年来,这个生于昆明、身上有一半广东人血统的画家在成都度过幼年,在云南晋宁插队两年,在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度过四年画布上的时光。紧接着,张晓刚回到昆明,先是待业,继而在一家玻璃制镜厂做建筑工人,然后去昆明市歌舞团任美工,其间还到过深圳一家装饰公司打工并被炒鱿鱼,他回到西南故乡,直到1986年如愿被调回川美师范系执教。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逃离重庆、成都、昆明,移居北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某种说不清楚的力量把他推到中国当代艺术家行列中的前排,成为最受瞩目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如今张晓刚坐在上千平方米的工作室的一张沙发里,又需要再一次回忆并讲述他的过去。30年来,他所经历的所有挫折、压抑、彷徨、愤懑、孤独、无聊、虚无、颓废、忧郁、忐忑、得意、伤痛……都成为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他成为一个样本,无法推辞,无法遮掩,无法忽略,无法逃避——讲述本身成为他的工作。
他永远活在时间差里,而且,“这个时间差有20年”。
《描述》,2008年9月17日,彩色摄影、银色签字笔,油彩,180 x 350cm
在这上面张晓刚写道:“……人们在这个疯狂多变的年代,发自心底深处的恐惧却恰恰不是因为贫穷,想到在那真正一贫如洗的八十年代,几个朋友,身上除了皮就是骨头,喝着劣质的烧酒,虽然苦闷,迷茫,每天都要骑着单车在城市里胡乱瞎逛一圈,回到自己的小屋,捧着一堆并不真正明白的书狠狠地看,但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贫穷。我也知道,现在若对人说这些话,显得过于奢侈,甚至显得‘矫情’。也许是这样的,不要去奢望‘记忆’真的能给我们今天带来多大的力量,不是么?在今天看来,‘记忆’不过也是一个可以消费可以为我们带来物质的产品,仅此而已,若不能带来这些,人们自然会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将它关掉……”
四年前他的母亲去世,整理遗物的时候,他才发现早年写给母亲的回信全都被她烧掉了,仅有的一封,被夹在仅存的两本日记本中的一本里。那是巨大的遗憾——从1986年到1996年,这对母子之间的通信长达十年,平均每个星期都要往来两封信甚至更多。由于在“文革”中受到刺激,母亲常常出现幻觉,认为自己的儿子经常在外被人打、被人迫害。她把那些担忧写到信里,而张晓刚能做的就是不断地“编”另一套故事,说服母亲自己完全没有遭遇这些。
但不管怎么样,母亲都把所有信件烧掉了。张晓刚说,那是上一辈人的习惯:不能留下证据。他远在昆明老家、现年94岁的父亲早年做过地下工作,现在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仍是把一串钥匙挂在身上——即便对家里人也要有防范意识,这是一个习惯。
长久以来,张晓刚都是一个积极的书写者。他的日记写到上世纪90年代才停止,而整个八九十年代的通信则可以摞起一个人高的高度。与朋友们——周春芽、毛旭辉、叶永青等人的通信在2010年集结出书,题为《失忆与记忆》,如今已几乎断货,在网店上甚至被炒到了两百多元一本。
据称,那套梳理他从1981年至2013年艺术生涯的四卷本《张晓刚:作品、文献与研究》将于明年年初出版,时下他正忙着的事情就是审校书中的文字。他发现那里还有太多的细节需要确认,太多差错需要纠正,最后他不得不亲自写一遍自己的“回忆录”。
我问他记忆力怎么样,他说:“过去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的朋友、策展人吕澎劝他出版《失忆与记忆》一书时说,“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一个交代”;对于自己的过去,那些已经远去的带着黄金色彩的人生,张晓刚觉得,写下来,说出来,“现在好像到了刚刚好的阶段”。
(《描述》2008年9月18日,彩色摄影,银色签字笔,油彩,180 x 350cm
在这件作品里,张晓刚用一封信写给妈妈的信来打消妈妈的担忧:“实际上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虽然一个人远离故乡,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工作、生活,甚至朋友很少,相对孤独一点,但这样对我是有好处的。至少这样可以使我能够获得某种安宁,让我能专心地学习、工作,远离过去喧嚣繁杂的生活,使我能好好地清理一些自己的想法,反省自己的许多行为——这也是我为何要突然选择到这样一个实际上我并不喜欢的城市里来,并且待在这个城市的边缘角落的原因之一。”他还引用了《尼金斯基手记》中的几段文字,其中一段写道:“我要写很多,因为我要向人们解释生命和死亡的意义。我无法写得太快,因为我的肌肉累了,我已经无法控制。我是个殉道者,我感觉肩膀很痛,我喜欢写作,因为我想借此帮助别人。但是我无法写作,因为我感到越来越疲倦了。我想停下来结束,但是神不允许。我要一直写到神要我结束为止……”)
我们这一代艺术家都有一个习惯:需要找一个“假想敌”。我们家四兄弟从小在一起画画,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不是说我有多高的天赋,我觉得可能是我需要这个。我从小就害羞,在班上属于要是老师多表扬两句都要感动得哭起来的那种人,所以唯一能让我自信快乐的就是画画,画画能让我投入到另一个世界里,忘却现实。初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喜欢文学,因为没觉得自己画画有多好,所以那会儿的梦想是当作家。后来因为偶然的机缘,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林聆,他是部队里的职业画家、我爸的朋友。我一下子就发现跟画画这个缘分没法解,后来就让我爸带我去拜师,我爸不同意,我居然自己跑过去拜师了。
我之前连铅笔怎么削都不懂,用什么纸也一点概念没有,他就从素描、静物写生开始教——昆明没有人这样教画画的。给我看的东西也不是“文革”那一套,而是欧洲古典的那些大师,像维米尔、门采尔,所以我骨子里受影响的也是欧洲这些东西。一直到1992年我第一次去欧洲看原作,才了解那是什么感觉。
1982年,我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就像后来跟人说的,那时候有“三座大山”压在头上:一是没工作,前途渺茫;二是我跟我爸的关系特别紧张,觉得回到家没有温暖;三是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回到昆明,我谁也不认识,那一年又是我的本命年,所以觉得很孤独,很难熬,不想画画,也不知道画什么。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画画可能没有那么崇高,已经变成一种职业了,但在我们年轻那会儿,做艺术是很奇怪、很另类的一个行业。你说你是艺术家,“艺术家是干吗的?”没有人觉得艺术家是一个正当的职业——尤其当你不在一个“单位”里的时候。
像我毕业后在昆明市歌舞团做美工,本职工作是设计服装和布景,演出的时候去拉幕,画画只能是业余爱好。别人会觉得,你是画画的,那你对我们有什么用?——我结婚的时候你可以画一张画送给我。所以我送了好多画,那会儿人家觉得你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艺术家都有一个习惯:需要找一个“假想敌”,然后才有一个目标去奋斗,或者去批判。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没有人是为了一个“敌人”去生活的,即便那个东西还在,它也不像敌人,更多的是一种诱惑。比方说资本进入艺术领域以后,它带来的是快乐、是诱惑,你说它是敌人?不是,它变成神了。
(从左至右分别是:1981年张晓刚在四川美院的宿舍;1986年至1988年张晓刚任教四川美院期间的居室兼画室。)
我觉得艺术应该像水,慢慢流淌,像一条河。其实我一直都处在边缘,包括1986年回到四川美术学院任教之后的十年。在那儿我没有朋友,领导也不太喜欢我,他们会跟别的青年教师讲,不要跟那个人来往,他那套东西不能卖钱,又没什么意思。能够在一起聊天的就只有叶永青,其他的时间就是上课,上完课就回到房间干自己的,也不走动,搞搞关系什么的。时间过得也很快。
那时候我受存在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但存在主义不是唯一的,那会儿什么书都看,现在想想,真看懂了吗?但是年轻嘛,喜欢现代艺术,你得学很多东西,先把自己武装起来,面对那个假想敌你才有武器把自己保护起来。所以看很多现代主义的书,也喜欢荒诞派的戏剧,后来特别喜欢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因为他写的完全就是我们学校里的感觉——一个小地方里人和人错综复杂的关系。
因为喜欢现代的东西,然后就有了一些朋友,后来就成了一个小团体,在这个小团体里自己给自己打气,跟社会保持很远的距离,就像形成一个真空带一样。后来大家解读为“反抗”什么的,我觉得太夸张,其实更多的是在自救、自卫,只要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你就是成功的。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看老一辈怎么走过来,我们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参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都没有进入国内的艺术圈里。现在觉得很荒唐,但那时候我们这一类作品几乎没有展出的机会。我的作品其实是很保守的,不属于那种实验性的、前卫性的东西——我对太前卫的东西进入不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主流价值观里我就是属于边缘。
1996年上海第一届双年展,主办方让我参加,我专门画了三张油画给他们,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说不行,当时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审了稿,把我一个人给涮下来了。第二届上海双年展,他们又来找我,我问他们行不行,他们说没问题,结果又没消息;一直到2004年,我才参加了上海双年展。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出过省(参展),也习惯了,觉得我们这种趣味的东西跟他们没有关系,当时会压抑、会难过,但过一段时间就算了。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我出道是比较晚的,而且我们班又那么多“明星”(川美77级被称为艺术界的明星班,包括程丛林、高小华、罗中立、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等人)。1994年我才出道参加国际展览——那是一道坎,就像你领到了一张进入VIP俱乐部的门票一样,感觉一下子就进入了另一个圈子;到了2006年又是另外一道坎,我没想到我的画突然被拍得那么高,市场一下子把我推到了第一排。说实话我是很不习惯的,反而有点恐慌,我觉得我还年轻,怎么画价就弄得那么高,就像是一个死了的艺术家的价格。
2006年之后,当我们(张晓刚、王广义、方力均、岳敏君)被称为“F4”什么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艺术家了,那是被安排的,是人为的结果。这个名头好像是台湾的某个画商弄出来的,他们喜欢这种封号,当时不是有一个电视剧《流星花园》吗,他们就这样套用过来了。其实生活中我们四个也经常在一起,我们自己都有点嘲笑这个,但也无能为力。后来市场越来越火,我们就从“F4”变成了“四大天王”,好像无形中我们变成了一线艺术家。原来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玩,也不以成败和经济论英雄的,结果那几年之后,有一线二线的感觉出来,就慢慢听到有人附和,有人不满,有人表示要奋起直追。
我第一次对市场有了很深的体会。过去的理解都是很肤浅的,觉得画完卖掉就是市场,后来才发现这是最初级的市场。后来听得多了,分析得多了,就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玩这个游戏,只是借了“我”而已。当中的很多体会,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比如说大家对你的艺术开始重新评估,也会有怀疑,你就变成了漩涡里的一个人。
我觉得艺术应该像水,慢慢流淌,像一条河,而不是像这样大起大落、风口浪尖,这样的事不适合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晓刚始终是忧郁的。在一张撕下来的稿纸上他曾经写道:“……我的艺术感觉一直倾向于某种‘封闭性’、‘私密性’,一般来讲,我总是习惯于‘有距离地’去观察和体验我所处的现实,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沉重的历史。这样讲,并非意味着我要试图去接近一个‘愤世嫉俗’的遁世者,也许这完全是自己的性格和气质的原因。”)
我永远活在一个时间差里,而且这个时间差有20年。
2006年市场起来之后,大家才认识到《大家庭》的价值,但那都是我十年前的东西啊。说实话我有一点悲哀,因为我创作《大家庭》的时候,身边听到的都是批评。后来大家把它神话化,甚至把它当成我最具代表性的东西——2006年到2008年那两年,几乎隔一天就有一个采访,就谈“大家庭”。我也给他们看我的新作,但大家对那个没兴趣,他们只对哪一张画卖多少钱有兴趣,我也只能理解,但我真的很累。
我只能想,艺术家有另一个时间表,他走在另一个时间里,但是现实常常要把你拉回正常的时间,来谈你的人生。
可能艺术家已经50岁了,但他还活在另一个时间里,体验不一样的东西,就像欧洲讲的,艺术家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传递者或转译者,所以艺术家的时间不是正常的时间的概念,有的艺术家慢,有的艺术家快,有的艺术家50岁才反应过来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而像梵高这种,三十几岁就完成了。所以我觉得自己一直处于某种分裂的状态,就是一方面我要回到现实来谈我十几二十年前的人生经历和想法,人走了之后,我又要回到另一个现实中,去创作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我永远活在一个时间差里,而且这个时间差有20年。
我很羡慕那些把时间控制得很好的人,他们面对媒体和市场的时候活在当下,而且一边创作,一边制造另一些神话出来,好像他永远都活在当下。而我,我觉得自己所面对的,就是不断把我拉回到过去。
我不是一个对当下敏感的人。画画不喜欢写生,照片也比现实更能让我联想到艺术,所以我永远都在画过去。我画我小时候看过的物品和环境,画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时间长了,就变成一种语言符号了,社会上就给我假定了一个角色,好像我是画历史的,我说我不是一个还原历史的画家,甚至都不是一个肖像画家,别人不听,我也就无所谓。
对我来说,当代艺术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精神的概念。从《大家庭》之后,我从语言形态到整个关注点都发生了很大的一次转变,我也在不断地发现自己,最后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不属于那种适合做观念艺术的人,也不属于研究语言学的范畴。追溯起来,我最早跟随的是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关注生活和内心感受,关注梦境甚至文学和音乐,所以我的工作不是一件作品一件作品去做,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做。
所以《大家庭》之后,我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回顾,而是要探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我把它放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它更有说服力。再后来是《里与外》系列,思考的主题从《大家庭》的公共领域进入一个更私密的状态,就是表达我们这个时代对人的记忆的损害,以及人有意识地去遗忘这两者之间的悖论。里与外本来是空间概念,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它们都是被意识形态美学所影响的室内和室外,所以户外的风景有喇叭,室内有绿墙,这些物品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美学的氛围。这个系列画的时间最长,现在还在做,比如《描述》系列,表达的就是对媒体的感觉——我拍了一些电视画面,然后用写日记的方式覆盖它,但核心还是要找个人与公共价值形成的矛盾。
在中国,艺术家没有完全个人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你不是完全的一个个体,你处处都会碰到公共对你的影响甚至干预,所以我的工作不是去表达我和别人怎么不同,而是要找我和社会的关系,我被改造或形成了什么样的个人价值。现在年轻的艺术家可能更个人更国际化,但我做不到,抽离现实去做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艺术家,对我来说就抽空了,我要和我的历史、现实发生关系,它不是书本里的,它是现实中的。
传统的中国文人,如果仕途没有了,就退到艺术里来,或者从儒家退回到道家里来,这是他们的处世原则。但现在你是无处可逃的——你能退吗?或者,干吗要退?有的人采取不合作或反抗的方式,我选择的是自在自为,不跟你发生正面冲突,也不会随波逐流,我有我的底线和原则。我做不了一个革命斗士,甚至也不属于持不同政见者,但我是一个艺术家,这个环境给了我什么感受,我就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我不回避它。
(2014年10月22日,张晓刚在何各庄的工作室内。深秋的太阳下山赶早,他把工作室内的灯全部打开,有那么一瞬间,他抬头,在白炽灯下留下剪影般的侧脸。)
艺术家一定要有无用的时间观、无用的价值观。
二十来岁那会儿,我天天读西方的书,想的问题很抽象,但1992年到西方看原作的时候才发现:梵高是个荷兰人。这有一种雷击的感觉,你知道吗?看书的时候,你不会去想他是什么国家的,只是被他的作品和人生感动,但你到那儿一看,突然发现他是个荷兰人,而且是有一身毛病的人。所有那些我认为了不起的大师,一瞬间全部变成了“外国人”,这个打击很大。然后你会想,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还会被他打动?那肯定有一个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艺术。
1992年,我突然领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艺术”、“国际化的艺术”,这是我们的奢望,我们希望艺术可以超越地域,但其实所有的艺术都跟它的环境、传统、教育、民族、文化有关,你摆脱不了。
我觉得伟大的艺术不仅看它表达了什么,还要看它怎么表达,表达的高度有多高。同样画一个水果,有的人就是画得好,那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天才,但这个伟大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意义,不仅仅是天赋的问题。在今天这个环境里,你很难去谈独特性,因为你总是受到方方面面文化的影响,利用文化形成你自己的资源,这是我们今天做艺术的方式。怎么把它表达成一种比较高端的文化的概念,这是一种能力,需要天赋,也需要机会。中国大量的艺术还处在山寨的阶段,还没有达到创造性的阶段。
我觉得艺术是对现实的超越。曾经有一段时间,从1986年到1989年,我完全生活在一种超现实的状态里,喜欢文人绘画以及原始绘画,也画了一些很浪漫的神神鬼鬼的画。但在那之后,我发现自己脱离不了这个现实,但又不愿意介入这个现实,这也是后来我要去寻找身份认同、寻找自己的原因。
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无所谓的话,其实挺可怕的。美术史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美术史永远是讲到20世纪初就截止了,后来都不敢讲。中国艺术界有美协的艺术、有学院的艺术,还有所谓的当代艺术,还有国画——今天的国画那么堕落、腐烂,有谁去面对它?媒体总是关注当代这一块,但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要说钱,国画那一块赚的钱太多了。所以我们了解的现实是真的现实吗?其实不是,媒体上你看到的都是小众的东西,并不是这个社会的本质。
谈到时间,就像之前说过的,我觉得做艺术家不应该受生理时间的影响,如果你用北京时间、伦敦时间什么的来做参考的话,可能会放弃很多追求。所以艺术家的时间表是根据他对艺术的体验和认识来走的。你看为什么有一些画家办展览特别慢,因为他体会一种东西可能要一年的时间,而做装置的、做行为的、做观念的时间就快,形态不一样。
有时候,我坐在工作室一整个下午,什么都不干,可能就翻翻书,听听音乐,发一会儿呆就走了;没感觉或没状态,就回家看看电视。我夫人有时候不理解,说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还在那儿,但对于我来说,我还在另外一个时空里。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下午四点你在发呆,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在浪费时间,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半夜四点感觉来了,怎么办?是该睡觉,还是该工作?
我觉得艺术家一定要有无用的时间观、无用的价值观,如果太精明,太实用了,往往就做不好。他可能会成为马云那样的人,但成为不了一个好的艺术家,因为好的艺术家的时间、价值都是消耗在无用上的。
我靠画“家庭”出名,但我的家庭又总是有很多残缺,我觉得很古怪
长期以来,我不断去想虚无这个问题,它就像身上的细胞一样,只是随着气候季节温度的变化或大或小。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细胞大概在二十岁左右就形成了。有时候虚无到真的觉得不想要了——我有几次这样的经历,就是到达抑郁的边缘,如果再往前走,我可能真的就抑郁了,那就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
这种时候往往发生在半夜,尤其是午夜,所以那会儿可能是音乐、写信挽救了我,到第二天太阳升起,一切重新开始以后,我就开始画画了,把对虚无的记忆描述下来,这时虚无可能又形成一种新的意义。你可以说那是恶性循环,但它无形中变成了你艺术生命的一种流程。
在我的作品里总有那么一些东西,别人看到的可能是伤感,在我看来其实是虚无。对时间的虚无,对现实的虚无,对死亡的恐惧,它们始终伴随在我的作品里,就像癌细胞,长在里面,碰到一个同样有癌细胞的人,就可能会引发化学反应。
我觉得画画是要用时间堆起来的,不是说有想法就能画得出来,可能往往前面五张都不是最好的,到第五张、第八张以后,感觉才真的出来一些。我画画很慢,比如说有一个新的想法出来,我头几张画是很烂的,我自己很清楚,但是没关系,这是必经之路,你必须先死而后生,等画到自己都烦了,可能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大家庭》就是这样出来的,开始的时候一直找不到方法,后来就拿一张画来,每天就看那一张画,死抠。
比如《大家庭》系列里底色之外的颜色,我是希望有一点浓烈的东西突然很意外地出现在那儿,而不是对照片简单的复制。过去我们讲找亮点,我就是要找这么一个点,要么是一块疤,要么是一个色彩,我把它画得像痕迹、像光斑一样。其实最初是缘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就是觉得不能让画面太正常了,把它破坏一下,我就觉得很舒服。从视觉语言上来讲,这样的破坏形成了一种对比,就像危险中的平衡一样,在一种非常和谐的环境里有一点点不和谐,你反而觉得这个画面有生动的东西。
我可以很浪漫地说,亲情和爱情都是我创作的源泉,但我也可以说它们不会左右我的艺术。我只能说那种影响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比方说我一直渴望有家的感觉,但是我最欠缺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一直在追求家庭的感觉。
从小父母就很忙,“文革”时又被拆散,有几年我父母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兄弟几个就交给隔壁的“代管”,这是我童年对家庭的记忆。后来成年了,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好不容易组合成一个“家庭”,结果没几年也解体,我又到北京来漂,又组合成另外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到现在感觉还不是很完整,所以这是亲情和爱情对我的生活的一个作用。
(张晓刚的雕塑作品《男孩2号》,35ⅹ20ⅹ20cm,绘画雕塑,201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被谈论最多的永远是“大家庭”系列,张对此只能深感无奈。)
我靠画家庭出名,但我的家庭又总有很多残缺,我觉得很古怪。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残缺,导致我去关注它、在意它,下意识地表达它。
至于我父亲,他年龄大了,我年龄也大了,我成了父亲,也就理解他,我们之间温情的东西也就慢慢多了起来。跟我女儿呢,原来没有代沟,现在反倒有了。这两年她会说,“你懂什么,你们那一代人”。还好,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想抹平这个感觉,她想多了解我一点,我也想多了解一点她的想法。
我跟女儿尽量像朋友一样相处。她也学画画,我觉得她比我有天赋。不过她现在这个阶段就画动漫,还是喜欢很唯美的东西,少女嘛。但是我不能对她这种唯美表现出一点点嘲笑的感觉,否则她会很生气。
你问我如果把艺术圈当成一个江湖的话,我在这个江湖里是什么样的地位?我想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老画家,一个一直没有成熟的老江湖。我的第一件作品是在1981年,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走了那么多的路,经历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乡土艺术到批判现实主义,再到85新潮和现代主义运动,最后到市场经济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时代),我是一个持续在场的人,这种人可能已经不多了。
早年我也写诗,但其实那是青春期的几句牢骚,谈不上诗。但我喜欢看诗,原来最喜欢的诗人是拜伦,后来一想,是喜欢他这个人。我觉得诗歌是很深奥的、是我很崇拜的一个东西。
读书现在是越来越少了。看书比读书多,这个意思怎么讲?就是我也在买书,但就是看看、翻翻,大概感觉一下,不像原来那么认真地读,现在读不进去了。一个可能是现在好书太多了,无从下手,读不完;不过主要原因还是碎片化的交流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看每天几个小时在微信上面看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跟人聊天、开开玩笑,很快所有的状态就消耗完了。
我喜欢的音乐很杂,流行、摇滚、世界音乐都听,好听就行;但重金属的接受不了,偏后摇、乡村一点。而且很奇怪,我对爵士乐找不到感觉,好多人以为我喜欢爵士乐,送我爵士乐的CD,但我又不好意思说。
摇滚里面,平克·弗洛伊德肯定是我的经典之爱,我喜欢史诗一样的,或者带有个人吟唱式的软摇滚,但华语的摇滚实在是……老崔是一个里程碑,其他的始终没上到那个档次。
早年的朋友,像周春芽、叶永青、毛旭辉这几个,联系一直都没有断过。我们的关系不像同行了,就是同乡,有时候都忘了大家是画家了。如果只是同行的话,你对他的艺术会有很多看法,同意还是不同意,喜欢还是不喜欢;但现在这种关系就会忽略他艺术方面的东西——反正都是朋友,哪怕你不喜欢他的艺术,也不会影响对他的看法,反正觉得是你的就是对的,你觉得好就好——没法谈艺术了,这也是一个遗憾。
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喜欢艺术,不一定是画画,但得是跟文艺相关的,要么是文学,要么是电影,其实我最想做音乐——如果下辈子还要做的话,我愿意做一个音乐家,或者,做个摇滚诗人也不一定。谁知道呢?
曹飞跃 中外艺术
(来源:NO ART,文:曹飞跃 ,摄影:曹飞跃 ,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頻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