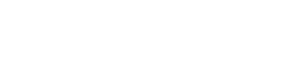纽约时间5月6日下午,被誉为“时尚界奥斯卡”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MET GALA盛大开幕,今年的主题是“坎普:时尚笔记”。神秘而难以定义的坎普美学究竟是什么?看完这篇文章,你就懂了。

2019年MET GALA红毯现场
聚焦:从T台到红毯
今年的MET GALA红毯为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奉上了近几年以来最为戏剧化、最夺人眼球的一场视觉盛宴。各路名流卯足了劲儿打扮自己,暗暗打响了一场镜头争夺战。
维秘超模Josephine Skriver在红毯上
本届舞会的头号联合主席Lady Gaga以超级夸张的坎普风格造型完美切题,向观众交出一份满分答卷。身着超大号亮粉色Brandon Maxwell礼裙的Gaga霸气外露,与身后撑着黑伞、提着裙摆的助手一同构成了一场极为戏剧化的小型行为艺术表演。
作为极繁主义时装潮流的开拓者,Gucci现任艺术总监Alessandro Michele把坎普风格拿捏得恰到好处,与流行歌手Harry Styles一起致敬了上世纪后半叶的性少数坎普先锋和华丽摇滚造型。
左:Harry Styles 右:Alessandro Michele
演员Michael Urie与Zazie Beetz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雌雄同体”的套装作为“战服”。一半笔挺西装,一半优雅礼裙,将坎普美学的去性别特质诠释得淋漓尽致。
左:Michael Urie 右:Zazie Beetz
在奥斯卡红毯上以无性别造型惊艳全世界的男演员Billy Porter,则再度展示出了超强的造型驾驭能力。被六位半裸猛男抬进红毯的Billy,“cos”了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造型,金光闪闪的衣着和一对金色翅膀无比华美,赚足镁光灯。
今年的MET GALA红毯何以如此夸张怪异,甚至有点令人难以接受?如果以日常生活的审美视角来看,这些造型很难被定义为美。然而在坎普美学的世界中,这些千奇百怪的造型各有其美,且美得独一无二。只有真正了解了何为“坎普”,我们才能真正“get”到这场视觉盛宴的超凡美感。
身着Viktor&Rolf高级定制的演员Hailee Steinfeld
溯源:从圈内“黑话”到美学趣味
“坎普”(Camp)一词的美学定义来自于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于1964年发表的文章《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 “Camp”)。她敏锐地发掘到这一当时仅仅流行于性少数人群中的圈内“黑话”,定义并扩大了它的美学内涵,最终将它推向主流文化视野之中。
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
当时,性少数圈子中盛行一种视觉效果极为浮夸繁复的行为方式和穿搭风格,他们用丰富的色彩、奢华的配饰和混杂的单品装饰自己,行为刻意矫揉,视觉效果上满满当当,极具冲击力。

上世纪50年代的一场私人生日派对中的性少数装扮
当人们在地下俱乐部看到这样“花枝招展”的场景时,“camp”一词便脱口而出,于是这个源自法国俚语“se camper”(以夸张的方式展现)的单词逐渐被用来形容这一独特的视觉景观。
“Camp”逐渐被用于形容这一“花枝招展”的视觉景观
苏珊·桑塔格打破了“坎普”的圈子界限,在她看来,坎普趣味的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性向局限,而能够代表一种指涉颇广的美学风格,其萌芽早已出现于历史上的诸多艺术流派之中,但却从来没有被严肃解读过。
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作品《年轻病态的巴库斯》已然体现出坎普趣味的雏形
总的来说,坎普趣味的表现功能远远大于叙述功能,抛弃内容而凸显形式,兼有对病态细节和夸张形式的追求,着意于通过醒目视觉元素的堆栈而展现一种满满当当的纯粹美感。
英国鬼才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的作品充满坎普色彩

莫斯奇诺(MOSCHINO)2019秋冬系列以游戏和戏剧的玩味态度回应着坎普命题
坎普美学并不是要向人们传达内容和意义,而是倾向于给人们直接的外在视觉感受——人造的而非天然的,美学的而非道德的,大众的而非精英的。由于坎普的反内容性质,人们对它的认知只能止步于视觉风貌的大致描述——矫饰的、极繁的、堆栈的、奢华的……
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的暗黑坎普设计
“坎普”是一种新感受力,一种现代审美方式,一种新文化趣味,但它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漫长的文化铺垫和风格推演,直到后现代思潮在上世纪60年代异军突起,坎普美学才获得其“合法性”。
“坎普“是一种现代审美方式
流变:从卡拉瓦乔到Lady Gaga
坎普美学在艺术史中的身影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卡拉瓦乔的作品呈现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与自然截然不同的气质。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摆出高度理想化和神圣化的姿态俯瞰众生,而是以肉欲的、世俗的身体平视观众。
卡拉瓦乔《鲁特琴演奏者》
在名作《抱着水果篮的男孩》中,卡拉瓦乔格外着意于对男孩右肩的细致描绘。画面中,男孩以十分不自然的姿态展露着自己的右半侧肩膀,刻意凸显着肩膀上的肌肉轮廓,矫揉造作的同时又流露出些许情欲的意味,与脸上耽于欢愉的表情相得益彰。
卡拉瓦乔《抱着水果篮的男孩》
另一幅《年轻的酒神》同样能够以坎普美学的视角来进行解读。通过右臂上下的大小对比,观众能够发现酒神正以扭曲的姿势努力让右肩前倾,因而整个右半边上身在画作平面上呈现出失调的比例。酒神微醺的眼神意味深长,已然摆脱了神性的束缚,以世俗的姿态发出共进一杯的邀请。
卡拉瓦乔《年轻的酒神》
随后兴起的巴洛克与洛可可将视觉上的繁复、奢华和曲线运用到了极致,用视觉元素的垛叠创造出体量庞大的美学景观。这种极繁的甚至是过载的审美趣味,日后成为坎普美学最为标志性的视觉特征。
意大利雕塑家贝尼尼的巴洛克风格作品《圣特雷莎的狂喜》着意刻画出人物矫揉的体态与表情
洛可可装饰对于精致细节的病态追求同样具有坎普的意味
上世纪20年代被称为“咆哮年代”,经历一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工业发展,人们的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普遍大幅提升,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就完美再现了这一时期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
《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这一时期的上流社会女性热衷于复古风格的奢华舞会穿着,电影女主角黛西在社交场合中的着装就颇具代表性。苏珊·桑塔格认为这种戏剧性的复古穿着正是坎普趣味的典型表现。
上世纪20年代上流女性的着装正是坎普趣味的典型表现
上世纪50年代,坎普以反抗精英化和刻板化审美传统的姿态横空出世,通过运用被称为“坏品位”的浮夸视觉元素来实现对这一批评本身的反讽,最终在迷思中“负负得正”。先是在苏珊·桑塔格的先锋性定义下正式获得其合理性,之后便进入到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开始自成逻辑地自发性繁衍。
华丽摇滚成为坎普美学获得合法性后的第一个产物
上世纪70年代的华丽摇滚将坎普视觉与颓美摇滚融合起来,呈现出极为华丽丰满的视听效果。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百变造型就是对于坎普风格的身体力行。
大卫·鲍伊的华丽摇滚造型是不折不扣的坎普产物
2018年上映的美剧《姿态》(POSE)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纽约的社会生活与舞会文化(Ball Culture)。社交舞会中的人们费尽心思地用华丽复古的妆容和服装打扮自己,以求获得舞会女王的称号。这些充满造作感的表演和装扮同样也是坎普趣味的产物。
美剧《姿态》对上世纪80年代舞会文化的还原度极高
英国鬼才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可以说是坎普美学的集大成者。在极简主义盛行的新世纪初,他用极尽浪漫华美的设计冲击着人们的眼球。“人们似乎不再盛装打扮自己了,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他的每一季发布会都展示出截然不同的视觉主题,其“坏品位”设计也总能够成为人们的目光焦点。
约翰·加利亚诺将矫揉造作的极繁设计发挥到了极致
坎普始终以小众趣味的形式弥散在文化脉络之中,它代表着后现代精神对于高雅艺术的解构。坎普的追随者抛弃了道德上的重负,以游戏和戏剧扮演的态度武装自己,沉浸在艺术和美带来的纯粹感官愉悦之中,从而超然于正统体制对艺术的严肃性解读。
Lady Gaga自出道以来就成为坎普美学的忠实诠释者
是坏品位?还是好品位?这一命题在坎普的逻辑中本身就是吊诡的。坎普对一切美学元素一视同仁,认为更重要的是表达自我。接受坎普美学的人都自足、大胆而愉悦,在热衷于坎普的背后是他们对生活与美的纯粹热爱。
自2015年上任以来,Gucci创意总监亚力山卓·米开理(Alessandro Michele)便一步步将复古浪漫的极繁主义风格打造成主流时尚趋势,坎普美学第一次以集体形态出现在核心文化语境中,成为这个时代文化诉求的代表。
Gucci开启了极繁主义的集体性潮流
坎普美学以“坏品位”的姿态长期站立在精英艺术的对立面,通过逻辑自洽的视觉表达来传递对艺术权威批判的“无所谓”态度。坎普美学无关道德,无关宏大叙事,而关乎生活的仪式感和趣味性,关乎超越社会规训的个人表达。
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穿着和生活么?不妨试试“坎普”,不用在意好坏之分,不用讨好所谓的“大众审美”,用繁复而鲜艳的元素装点寡味的生活吧!
原创: 路子杰
文章来源: 时尚芭莎艺术微信公众号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頻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