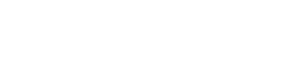1946年11月30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出生于当时还是南斯拉夫首都的贝尔格莱德。现在,她已经跨过76岁的门槛,再一次增强她身上的“行为艺术祖母”这个标签。
不过,对于这位从事行为艺术表演已超过50年的艺术家,年龄从不是个问题。
阿布拉莫维奇把身体当作主题,把时间当作媒介。她那张五官轮廓分明、富有表现力的脸庞,似是在诉说这个身体里只有顽强,没有屈服。
但接触过她的记者和作者在提到她时,形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她风趣、热情、带一点超凡脱俗。没有太多迹象表明阿布拉莫维奇在衰老。知名艺术评论家马丁·盖福特在提到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时,他这样写道:“她友好健谈,一点儿也不严肃,兴奋激动但又不失沉稳,看上去非常年轻。”
这些年,她还忙着开设一门课程,组织私人工作坊(Lady Gaga曾经参加),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准备一场表演(打破了学院252年中没有女性个展的纪录),在牛津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Gates and Portals》,在伦敦佳士得拍卖她的AR作品《The Life》,推出她的第一件NFT作品《英雄》,以及制作她人生中最大的装置——一堵40米长的墙。若不是因为疫情,她的工作还会有增无减。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切都变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表演“艺术家在此(The Artist is Present)”。每周六天、每天七个小时,阿布拉莫维奇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在这里坐了整整750个小时。观众可以坐在她的对面,凝视着她的眼睛,在沉默中相互建立一种深刻的情感联系。这项演出最终成为现象级的。它创造了85万名游客的参观记录。好莱坞明星James Franco也在门口漫长的等候队伍里。在与阿布拉莫维奇对视时,他哭了。
对于阿布拉莫维奇来说,最好的艺术是“一种非商品”,“你不能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它。你必须在那里才能体验它。”
很多时候,这种体验就意味着艺术家对自身肉体制造的痛苦,以及克服这种痛苦。从她最早的作品开始,阿布拉莫维奇就在探索身体和情感上的忍耐力、直面恐惧和暴露脆弱性。她将自己的早期作品定义为一个混合着禁欲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奇怪的组合。毫无疑问,这与她出生、长大的斯拉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都与传说、激情、爱、恨有关,和矛盾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第二年的《节奏5》(Rhythm5)的高潮部分,她躺在一个星形容器的中空区域,身体被石油和火焰包围着。刚进去她就失去了知觉,因为火把空气中的氧气吸走了。幸运的是观众里有位医生注意到了这一点,迅速把她救了出来。
在同一年的《节奏0》(Rhythm0)中,阿布拉莫维奇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惊险的一幕。她躺在那不勒斯的一个画廊里,旁边是一张放着72件物品的桌子,桌上既有玫瑰、蜂蜜等令人愉快的东西,也有链条、鞭子、十字弓和捕鼠器等危险物品,甚至还有一把上膛的手枪。在整个表演过程中,玛丽娜把自己麻醉、静坐,而参观者被允许用桌上的任何物品对她做任何想做的事。她的身上至今仍留有这场表演造成的疤痕。
她还说:“表现出自己的脆弱、毫无保留、不设防线,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我在纽约表演《房屋》(House)时,连续12天没有吃饭,有1200个人来看我的演出,他们都哭了。很多人看过一次后,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
原生家庭:一道必须穿越的墙
阿布拉莫维奇的家庭同样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混合了政治、权力、宗教和信仰,但唯独缺乏爱。她的父母是贝尔格莱德的大人物,身居政府高层,拥有一套当时南斯拉夫罕见的大公寓。她外公的哥哥是1930年代南斯拉夫东正教的主教,地位仅次于当时的皇帝。在他过世后,他那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被一直安放在贝尔格莱德的圣萨瓦教堂内,供信徒瞻仰。但她的父母都不是宗教隐士,而是投身二战的战士。他们曾与游击队一起抵抗纳粹军队,并且在战争期间相互救过对方一命。但他们的婚姻远称不上幸福。她的父亲出身贫寒,而她的母亲是会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表演的那种人。在阿布拉莫维奇八岁时,她的父亲离开了这对母女。对此,阿布拉莫维奇的结论很简单:“他们两个根本不合适。”
对于阿布拉莫维奇,她是在母亲的严格管束和命令式教育中长大的。“每天晚上十点前我必须回家,因为只有坏女人才会在十点后还待在外面。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洗涤剂,连香蕉都要。”这意味着她可以在行为艺术表演中割伤或用火烧自己,但结束后得马上赶回家睡觉。
这种宵禁一直持续到她29岁——期间她甚至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但她在结婚后也要住在自己家里,也要每晚10点前回家。终于,29岁这年,她离家出走了。她的母亲报了警,但在知道她的年龄后,就连警察也哄堂大笑起来。
她还很小就成为亲戚之间的“雇佣画家”,满足他们“想要向日葵、敞开的窗户和满月”或“更多的郁金香和鱼,让窗帘在风中飘”之类的要求。每完成一张作品,她可以赚取约合10-15美元的酬劳作为零花钱。多年以后,她的母亲自掏腰包,把这些画从亲戚手中全部买回收藏。这是这位母亲在面对阿布拉莫维奇时,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多愁善感”的时刻。
乌雷:无法回避的爱人 阿布拉莫维奇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时期:乌雷之前、期间和之后。乌雷(Ulay,原名Frank Uwe Laysiepen)与阿布拉莫维奇同月同日生,但比她大三岁。1975年,两人在生日当天相遇在阿姆斯特丹的机场,乌雷是临时负责接送阿布拉莫维奇的司机。
他们的化学反应几乎是瞬间的。高大的身材,摇滚明星般的骨感,张扬而怪异,是她对乌雷的第一印象。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家土耳其餐厅吃过晚餐后,相互看了对方的日记,然后“我们直接去他家,在床上躺了十天。”结束这段旅程回到家后,阿布拉莫维奇发现自己因为强烈的相思之痛“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当时她还住在贝尔格莱德的家里,要遵守母亲严格的宵禁规定,而且还没离婚。
从1976年到1988年,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开启了一段伟大的爱情故事。他们共享三种身份:艺术创作的合作伙伴,恋人,以及十二年游牧生活的伴侣。
这十二年间,他们在双人艺术上进行了多种尝试。他们或是穿着相似的衣服,或是一丝不挂,共同完成行为艺术的作品。在他们的第一场表演“空间关系”中,两位艺术家赤身裸体,在一小时的时间里持续奔跑和撞击对方,直到其中一人因为承受不了撞击而放弃。在“光明/黑暗”中,这对情侣面对面坐着,由慢至快相互扇对方的耳光,持续了六分钟。在“AAA-AAA”中,他们在双方的脸仅有几英寸距离的情况下对彼此吼叫,持续了约十分钟。
这些表演刻画了亲密和分离,也是对耐力的绝对考验。例如1977年,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在博洛尼亚的一间画廊里坐了17个小时,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两人背对背而坐,中间有座头发搭起的桥梁:阿布拉莫维奇的头发扎成马尾辫,和乌雷的头发连在一起。观众要到最后一个小时才可以进去欣赏。
她是阿布拉莫维奇 关于行为艺术:
“做行为艺术非常困难,而我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到了30岁时都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我不知道有谁在我这个年纪还在表演——他们不是死了就是病了。对我来说,它是最难的艺术类型之一,因为它是非物质的,它是基于时间的,它与情感和公众有很大关系,而且是一种非商品——你不能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它。你必须在那里才能体验它。”
关于创作灵感:
“我讨厌工作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陷阱。想法来源于生活。”
开始一件新作品的第一步:
“第一步是获得一个想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是一个让我开始的想法。我着迷了,最后,我说,‘好吧,我要去做。’决定的那一刻非常重要。但是一件作品总是以一个我不喜欢的想法——我害怕的东西开始,然后进入未知世界。”
艺术与恐惧的关系:
“要把身体用在行为艺术里,就必须面对自己的恐惧:对痛苦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这些都是艺术的主题,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你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被割伤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身体的极限能到什么程度?”
阿布拉莫维奇的工作时间表:
“我喜欢例行公事。它给出了一天的顺序。当我遵循常规时,我感觉很好。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变得不平衡。我喜欢修道院的规律性:僧侣们在日出前醒来,然后上厕所。然后他们进行冥想。然后早餐。然后他们会做体力活。我试着遵循一个非常相似的时间表。我喜欢早起。”
给表演艺术家的建议:
“首先,他们必须什么都不怕,也不惧怕任何人。”
如何保持长期的职业生涯:
“纪律严明。这需要难以置信的意志力和大量的纪律。我就像一个士兵,一个勇士。别叫我行为艺术祖母,就叫我勇士吧。我的传记被翻译成22种语言,书名是《穿墙而过》(Walk Through Walls)。我不是站在墙前,我正在穿墙而过,我从不放弃。”
关于在年近七十时学会开车:
“我这样做是为了独立。我总是把自己的恐惧当作一种超越恐惧的方式。”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