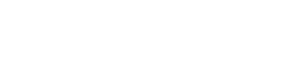大同大张《邮寄艺术96》的封面

大同大张《邮寄艺术96》的内页
《追问秤杆之重》作品草图

韩博《从波斯湾到大西洋》001
(韩博,当代著名诗人、艺术家、小说家、戏剧编剧与导演、旅行作家、策展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与新闻学院,美国爱荷华大学荣誉作家)

韩博《从波斯湾到大西洋》089
近些年,艺术家书受到了相对年轻艺术家的青睐。有的在艺术家书上做自己的实验,比如温凌《FMB》、烟囱《乞丐漫画》系列;有的将画册转化为艺术家书,比如韩梦云《夜》、胡伟《三个片段,从未被书写却或已发生的脚本》;有的提以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议题,比如张心怡《有刺》、程新皓《来自铁路的二十四封邮件》。这其中,摄影书是相当特殊的,几乎每位影像艺术家都会做摄影书,它为影像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比如汪滢滢《洄》、朱岚清《负向的旅程》。

常羽辰《诗三首》12×22cm 2021
自出版,开放版数

常羽辰《织机书》
20.3 × 22.9cm+12.5 × 27.9cm 2022 自出版,版数:50
常羽辰《珊瑚辞典》6.5×13×3cm
弓出版,2022年第一版
在2019年“第一回无界建筑季展览计划”中,欧飞鸿展陈了一本为都市白领定制的厕所读物,由手工木刻、家庭打印制作而成,起名 《刺纸》 。
《刺纸》原为月刊,后成为不定期出版物,欧飞鸿与 陈逸飞 邀请或收容了年轻的游牧者、安那其,以及无定的艺术家,并吐纳出相当多主题出版物:快递工、LGBTQ+、月经。 以《刺纸》《冯火》为轴心,这一端是艺术家群落,像菠萝核(BOLOHO)、44月报,那一段是出版组织,像迦梨kali、副本制作。

《刺纸5:经血不脏》
经由艺术书,弥散在我们周围的故事、精神凝结为文字 ,这就是罗森《花家地2014-2017》、宫羽与刘张铂泷《北京蘑菇寻找指南》等所做的工作。有时候,他们结成了灵活的团体,并在松散的同仁圈内交游,像更杳发起的浦口工厂。

罗森《花家地2014-2017》

罗森《花家地2014-2017》目录


当时代更替、理论新异,文化从业人将他们所认知、思考的信息,放诸纸张册页之上,这是他们成为艺术家、思想者,以及提出问题的人的时刻。而像《Be Water Journal 水象》《te magazine》这样的独立杂志,变成了思想与方法的池,它们从地下刚刚露出一点,犹如1990年代前中期涌现的丛书和刊物,今天我们仍然在从刘铮、艾未未、孙文波、欧宁的出版物中寻找某种发源。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脆弱的、观念的、去物质的、参与的、交流的艺术书。


后商:你如何理解艺术书之必要?
韩博:正常人的精神和知识需求,而出版领域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更杳:艺术书展中的艺术书也好,或者是独立出版物也好,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是对于主流出版视野的补充。首先我们得承认,有大量有意义的内容是无法被主流的出版版图纳入的。
艺术书的制作过程是艺术家对于某个阶段、某些主题探索和创作的整理。相较于美术馆展览,书册这一介质受时空限制更小,可以凭借书展、独立书店流通到感兴趣的读者手中。
相较于网络发表的数字形式,纸制品还可以承载更多维度质感上的要求,它的流通轨迹也是更可见的。而相比由出版社上架营销的一般出版物,这种流通过程更精准,你有机会看到你的读者是什么样的,有机会在书的流通过程中建立连接和对话。它是创作者直接与潜在对话者搭建的一个路径。
后商:艺术书几乎是全要素的,观念、设计、文学、印刷。艺术书对你的吸引力在哪里?
朱岚清:艺术书对于我的吸引力可能就在于它既可以涵盖所有要素,又完全不限于这些要素的束缚,它是没有标准的,唯一的标准就是艺术家觉得这本艺术书是否真正表达了TA的创作和观点。
艺术书就像一个可以放在任何一张桌面上或者捧在任何一个人手里的展览,它可以很小的成本制作,可以被很广的传播,可以触达到更大的人群,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家可以以实物的形式将一整个完整的创作历程保存并保留到未来的很长时间里,这个是艺术书可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朱岚清《负向的旅程》
朱岚清《负向的旅程》
常羽辰:可以列在艺术家书要素中的可能还有:写作,绘画,编辑,打包,零售,批发,托运,走私等等。在做书、卖书、教书的这几年中,我确实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而它跨越劳动分工的复合性确实让我喜欢。书展时常让我觉得自己有幸体验身心灵整合的经济行为:交流、交易和交心的重叠。而这每一环的工作中,我都是业余的,只有凭借热忱、直觉,以及慢慢累积的经验。
另一个吸引力是在这过程中交到的朋友。他们的理想给我启发,他们的踏实都让我敬佩。我以前不觉得艺术家书必要,只是自己喜欢;但我现在觉得必要。出版就是将作品公之于众,而现在,创造、连接和维护这个“众”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在眉睫。
后商:艺术家书(artists’ book)在中国并未得到系统地施展,但将艺术家书展开在相当大的图景上,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艺术家书的美好是什么?它的开放?它的多义?
韩博:艺术家书也是艺术作品,这就是它的根本价值。
爱米:艺术家书如同一件艺术作品,它可以是一本,也可以是批量的。我喜欢从内容到设计再到纸张印刷装帧都在同一个水准之上的艺术家书,没有一点的违和感,恰到好处,我自己也会常常收集这类型的艺术家书,并且时不时拿出来翻看。作为编辑,我肯定是非常看重内容的,但内容好,设计不匹配,我一般也不会收;反之,亦不收。
在大约十几年前,我曾经在工作的《城市画报》做过一篇关于“艺术家书”的报道,当时作者介绍的大部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艺术家书,也包括Printed matters的。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artist’s book”这个概念,艺术家书是非常纯粹的艺术表达,它和市场无关。从这一点来看,在当下以“市场”为一切目的的国内,艺术家书的概念是值得再被分享的。
后商:你如何参与艺术家的制作?
顾虔凡:最近去看了MoMA为艺术家埃德·鲁沙(Ed Rucha)举办的回顾展非常喜欢。鲁沙几本经典的艺术家书也以不同的方式展出其中,和他画了字、画了书、画了杂志封面的作品放在一起,有一种图像与文字共同漂浮于时空而幻化成不同形态的感觉。艺术家书也是形式之一,和其他创作一样。
我们“弓出版”在2019年和艺术家童义欣合作了他的《纽约钓鱼日志》,用一个像钓鱼工具箱又像鱼缸的盒子承载了他2015-2018年间在纽约的62次钓鱼之旅的纪录。这本限量出版物曾经参加过一次奖项评比,并没有入选,我听说有评委评价它“太不像书,像场展览。”这条落选理由我们其实听了都很高兴,因为做《纽约钓鱼日志》就是把它当作展览做的,而我们心目中的艺术出版物确实就是一种portable exhibition.
 童义欣《纽约钓鱼日志》弓出版
童义欣《纽约钓鱼日志》弓出版
温凌:2009年左右,我开始做漫画,纸上漫画,体验了从内容制作、排版印刷、装订销售等所有环节。我在家里打印,用订书机装订,在网上卖,在abC艺术书展上销售,整个过程给了我巨大的快乐。做漫画其实找出版社或者别人帮我做成画册也行,我为什么这么坚持自己体验全过程,是基于这样一个思考:在电子化之后,纸质的图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需要大家来想一想。
我认为,艺术书存在的必要在于这是物,它会散发电子以外的信息,它包含了无法言说的部分,用纸的质感、装订的方法、人去触摸的感觉。我把漫画书(艺术书)看成一个微型的雕塑、一个微型的装置,如果它足够精准充分,它就是非常有趣和美的。相反,如果它是概念化的、笼统的,它就是多余的和干扰的。
 温凌《54boy》2012
温凌《54boy》2012
 温凌《54boy》内文
温凌《54boy》内文
 温凌《Driving to IKEA》2021
温凌《Driving to IKEA》2021
 温凌《Driving to IKEA》内文
温凌《Driving to IKEA》内文

后商:也许是艺术家迷恋档案和书籍,也许是市场发达、经费充沛,也许是机构或环境为了确立自身,大概自2000年前后,画册配套展览制作,甚至出版,已经成为当代艺术业内的常态。与画册相比,以艺术家书为要的艺术书则很年轻,相对全面地发生是近几年的事情。为什么艺术书得到了年轻艺术家相对普遍的接受?艺术书之于画册有何特别?
韩博:国内艺术家书市场上大多数都是画册。很多这类载体并非因创作需要而产生,而是宣传需要。
罗森:不同于传统出版物,更不同于手机上的“屏读”,艺术书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呈现的载体,而是更强调语言和思想交流的目的。艺术书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对信息的编排和呈现往往是非线性的,很多艺术书编织了一种反复阅读的体验,它允许人们每次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书的世界,并从中获得情感和思绪的奇趣妙动。
相对于过去传统和当下流行的获取信息和沟通方式而言,艺术书是一种更直接的对人的经验、感受的表达、传播方式,它把一种感性的,基于审美现代性的直觉和批判要素接入到当代社会愈发复杂的知识和体验系统中来,这在一个越来越被流量绩效主义、AI等技术理性工具裹挟的传媒时代里是有必要的。
后商:艺术家书中最蓬勃、最渗透的是摄影书(符合严格的艺术家书定义的摄影书并不多),世纪初以来,中国摄影师也像欧美摄影圈那样做起了摄影书,并围绕摄影书发生了发表、展览、收藏、品鉴等一系列活动,摄影书几乎与展览并起。摄影书何以成为如此重要的媒介、展场、作品?
汪滢滢:《洄》的出版物之前有两版手工书,准确地说,因为第一版手工书,使得假杂志确定了《洄》的出版物计划。作为一个以摄影为主要语言方式的创作者,我一直认为,将项目整理成册,是为整个作品的句点。至此,一个作品可以算是完整的完成了。
因此,这个册子(可能是Zine,可能是手制书,或者是出版物),它也是项目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作用于独立创作之外的一个工作小结和展示。它的内容承载着艺术家与这个作品间最为原始的连接,艺术家可以将拍摄、绘画、文字不能及的情感和思考,通过添加其他形式,甚至于书籍的材料、尺幅、字体、排版、翻阅方式等等来构成最终的表达。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洄》的出版物在手工书的基础上作了很多适合印刷装帧的改变,但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作者手工书的一些想法。对此,我很感谢假杂志的工作,因为手工书转化到出版物,在书籍的设计上是非常有挑战的。


后商:独立杂志是目前传播度最广的艺术书。2010年前后,独立杂志大致迎来了一小波热潮,至今它虽相对退去,但也以不同形态融入了各种文化传播之中,它们部分加入了这些年的艺术书热,像我们熟悉的te magazine、Be Water Journal 水象、DEMO。是什么导致了独立杂志的生命力?
爱米:独立杂志的概念也有待确定。可能从9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就不断有各种“独立”出版的杂志出现,不管是个人独资或者有多人投资的小规模杂志。音乐、艺术、诗刊、电影都有。但是2010年前后出现的这些杂志,尤其是你举例的,多数是以视觉为主导的,这与当下大家的阅读经验有很大关系;
其二,编辑、设计师、摄影师在这些年都受到了很好的视觉教育,专业的教育,艺术的教育,策展等等,所以是一个整体的创意人群水准的提升,加上读者也偏向年轻化,读者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或自我吸收。但是,这类杂志应该不完全归属到艺术家书,它有艺术家书的一些特质,比如纯粹、比如热爱、比如同人志、比如对所有流程的把控,但杂志毕竟是批量的,没有那么多手工元素,更接近工业生产。
独立杂志的生命力,我觉得就是烂熟的那句话,“靠爱发电”。就如同那部电影《降临》里所描述的,最终是用爱来和世间万物交流,这种能量也许是非常强大的。
 Be Water Journal水象
Be Water Journal水象


水象第三期内文
汪滢滢:独立杂志的生命力,我认为主要是一个词:Unique.
后商:艺术书创作群体,怎样达成这样的、更好的协作?
汪滢滢:我不觉得艺术书的创作群体需要协作,至少在创作这件事上,保持自己的独立,不受过多的干扰非常重要。“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一些排斥和坚持。有趣的面貌越多,艺术书市场才会更有趣。
更杳:“浦口工厂”会与不同的实践者、艺术家和小组进行合作,交叉出版一些内容。比如与一帮有教育实践经验的伙伴合作了《打口教育学》,与“起风了”艺术社区和全职妈妈们合作了《母亲的选择》第二辑。基本上每一本书都是多声部的。如何把不同声音的交织以书册的形态存录下来并在流通中激发更多回音?我的搭档小朱一直在自出版和艺术书展方面很用心。

浦口工厂自出版书籍《打口教育手册》等
参加中间美术馆展览“火屿边缘”
顺带说一句,我认为就诗歌这类小众文体而言,独立出版也是一种自我救济的方式,因为很难争取到主流出版的一席之地。目前越来越多年轻诗人选择以自出版的方式出诗集,承揽设计、选纸、印刷等等环节,大家可能也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写作者之外的职能体验。从这个角度上讲,诗人也在溢出对于纯粹文字的依恋,进入到和更多媒介的关系实验中去,我觉得挺好的。

后商:在主流的出版和媒体陷入了某种困境、无处着手时,自出版成了某种替代,部分地承担了知识的更新、经验的更新,时新的选题、真实的人物、充满诱惑的故事,可以确保做出来的那本书能卖上好价钱。不惟中国如此,欧美市场中自出版的分量也越来越重,自出版人的专业素养也变得极好。自出版的向好,很像是艺术家与文化从业者对仕绅化局面的小小抵抗。请谈谈自出版的价值。
罗森:和“主流”出版物相比,自出版更依赖社群和跨个体性的传播,它聚焦、放大的是一种差异性的经验。它有非常强的实验性。可能一本自出版的读物在内容和出品上不一定能做到“主流”出版物把控的质量和内容严谨,但人们会关注这之中价值观和信息的重组。
有的时候未必严谨的东西包含着一种准确,就像说话(告白)一样,如果一段重要的话要等到两年或三年后才能跟对方说出来,它就错过了打中人的情绪要害和传播的契机,也就丧失了在社会和市场当中建立连接的价值和意义。自出版对目的和态度的表达更为直接,有它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爱米:我觉得“自出版成了某种替代”稍有偏颇。只能说自出版多了一些选题的思路和来源吧,扩大了传统出版的作者群而已。远远提不上“替代”。我认为,如果说内容选题是一片森林,自出版的书籍,不论是艺术家书或杂志,大概就是在森林里种了一点奇花异草吧。
后商:你如何做自出版?
冯俊华:我一般用“小出版”描述副本制作的工作,后来也接受了“艺术书”这个说法,这出于我对艺术的理解,它是关于人与人如何形成新关系的。我希望围绕副本制作的工作、以及从它出发的工作能产生某些新关系。
 副本制作和44月报联合出品的“1314”套组
《女狱花》(王妙如)和《汴梁城外》(羊二)
封套由欧飞鸿设计
副本制作和44月报联合出品的“1314”套组
《女狱花》(王妙如)和《汴梁城外》(羊二)
封套由欧飞鸿设计
后商:在做艺术书的过程中,你发现或见证了哪些问题?
罗森:艺术书制作成本过高,售价与消费者对一本书的定价期待较远,是很多有质量的艺术书没法走向大众市场的一个原因。
韩博:首先要梳理一下概念。我概念中的“艺术家书”不是批量复制的印刷品(就像我认为把油画复制了并不产生版画,只是产生印刷品一样),而应该由艺术家手工制作完成或手工参与创作。以艺术为内容的印刷品只能算是艺术出版物,无论有没有书号,因为每一本并没有独一无二性。不过,在中国的实践中,艺术家书似乎与独立出版物划上了等号,实际上是概念混淆,也是一种现实的无奈。
后商:从某个相对的视角来看,艺术书始终还是小圈子,这些年能加入这个圈子的做书人和读书人很少,能留下来的更屈指可数。但同时,艺术书在某些程度上,有与公众分享的属性:艺术家做书是为了传播,并在这种传播中使新的艺术发生。这些年,艺术书与公众的互动确实很大规模、高密度,很像是风潮。但是,公众的好奇、机构或资本的看好,有时候是走马观花,有时候是顺手利用。艺术书如何联结公众?
爱米:的确,不论是艺术机构、美术馆、画廊、个体、团体、公司,都在做有着艺术家倾向的书(也许不能统一称为艺术家书),和过去传统的画册有些不一样。新出现的这些书需要更多的编辑巧思、设计巧思。艺术书要联结公众是长路漫漫,因为大家的时间都被手机屏幕等占用了。但是,艺术家书确实因为它迥异于传统出版的各方面巧思,吸引了新的读者进来。
“艺术书展”是一个非常好的联结艺术书与大众的渠道,然而国内的情况大家也知晓,书在书展的比重是非常少的,也许10-20%,甚至有时候都不到这个比例。除了书展,艺术类、设计类书店也是非常好的渠道,让大众能触摸到实体书。这类型的书店在近五年十年越来越多,是个很好的趋势。希望大家都能撑住。


罗森:其实做一本艺术书,和正规出版一个书相比,门槛和成本是大大降低了的。它激发了人们对很多身边事情的一种想象、关注和好奇,同时也造就了很多素人创作者自生内在的表达动力。
很多时候,生动细节的直白流露比一个智性化的体系论述要重要。在我看来,艺术书的出现是让公众离书这个媒介的距离更近了。艺术书的作者大多不是受学院知识生产体系驯化的知识分子,而是跳脱出一些社会规范,热爱和关心生活的具体的人。
我认为艺术书被看好的价值应该是它潜在的伦理学层面的意义,而不是一种自我展示的美学。它背后呼求的是一种引发言说和理解共鸣的“文学共通体”。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其实回到了文学当中最基本的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我们不要把艺术书当成一个产品、作品、产业来理解,也许可以避免当它走近资本、市场,或进入机构化的语境中被评判和审视的问题。
后商:推荐一本你喜欢的艺术书。
汪滢滢:看过那么多艺术书,好的非常多,如果一定要只挑选一本,我依旧还是推荐苏菲·卡尔(Sophie Calle)的《痛》(Douleur exquise)。
罗森:《51摊》。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