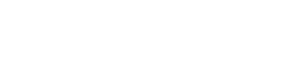大型芭蕾舞剧《敦煌》剧照
送你一朵足尖上的“敦煌”
——大型芭蕾舞剧《敦煌》再观感
于 平
上次看舞剧《敦煌》大约是一年前,是应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兼该剧总策划冯英之邀——她极富诗意地说:“来看看我们这朵足尖上的‘敦煌’ ! ”观后的我,写了篇《舞剧〈敦煌〉的文化守望》 ,刊发在2017年第11期《舞蹈》杂志上。今年的“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 ,冯英更是盛情相邀;看后才知道,经导演兼编剧费波近一年的打磨,舞剧《敦煌》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很有些百炼成“精”(精品)的感觉了!
“舞剧《敦煌》从人的主题入手,
真是没想到! ”
看过该剧的观众都知道,舞剧《敦煌》的主旨讲述的不是壁画、彩塑的造像,它所关注的是莫高宝窟的文物守望者。的确,在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推出勾脚、出胯、扭腰、手势丰富、头颈别致、表情妩媚的“S形”曲线的“敦煌舞”之后,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再把它移植到“足尖”上。好在冯英知道“深扎”对于“创作”的意义,当她和她的创作团队在敦煌“深入生活”之后,她说了这样一段话:“很早就有一个愿望,想把惊世灿烂的敦煌飞天艺术用曼妙婆娑的芭蕾尽情绽放……在与‘敦煌女儿’樊锦诗老师相遇、相识与相知后,我们才有幸窥见她及她身后的‘敦煌人’对这份世界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弘扬是何等的艰难与不易!我们越是深入了解,就越被‘敦煌人’痴情保护千年文化的故事所吸引和震撼! ”于是,冯英就把表现“敦煌人”作为“扎根人民”的一个具体措施。
经过一年的精心打磨,虽然剧中的主要人物有所调整和充实,但男、女首席演绎的仍然是吴铭和念予。吴铭作为剧中要鼎力刻画的“敦煌人” ,是以敦煌第一代文物保护者常书鸿先生为原型的。剧中的女主角念予,是位留法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她因为被一本关于敦煌的画册所吸引而来到敦煌,在敦煌又被倾心于壁画修复的美术家吴铭所吸引而产生恋情……常书鸿先生的女儿、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常莎娜女士在观看此剧首演后说:“这部舞剧演绎的就是我的父亲和我们‘敦煌人’的故事……舞剧《敦煌》从人的主题入手,真是没想到! ”这个“没想到”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是没想到舞剧《敦煌》主要讲的是“敦煌人”而非“敦煌壁画” 。
大型芭蕾舞剧《敦煌》剧照
“飞天”是“敦煌人”为之
坚守、倾情、奉献的“心象”
显而易见的是,“敦煌人”就是因“敦煌壁画”而得名、同时也因“敦煌壁画”而“扬名”的。编导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幕启之际,映入观众眼帘的便是在太虚幻境中飘逸扶摇的“飞天” 。这是用“三人舞”形态营造的“飞天” ——“飞天”的女舞者在两位男舞者或独支或合力或传导的托举中摇曳生姿……剧情稍后的展开告诉我们,那位“飞天”是剧中的第四号人物,称为“主飞天” ;而连同“主飞天”亦步亦趋的“三人舞” ,在展开的剧情中不断复现——一方面它成为剧情展开时环环相扣的“节点”,一方面它又仿佛是动态形象转换时形影相随的“动机” ;甚至它还是“敦煌人”之所以为之坚守、为之倾情、为之奉献的“心象” ,是另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道德的“召唤” !
这是一部二幕舞剧。第一幕由四场构成:起点是音乐家念予在巴黎的艺术沙龙中偶遇了一本关于敦煌的画册,画册中的“飞天”召唤她前往;于是她来到敦煌,却首先被“敦煌人” ——那些包括“飞天”在内的敦煌文物的修复与保护者所感动,更因此爱上了沉浸于壁画修复的画家吴铭;吴铭和他的助手水雯等执守于壁画的修复,因而放弃与念予同赴巴黎成就艺术梦想的机会;但自然灾害侵袭了敦煌,以吴铭为代表的“敦煌人”面临着技艺和意志的双重考验……
大型芭蕾舞剧《敦煌》剧照
构成第二幕的三场是:远去的念予成了吴铭梦中的念想,但他更多地却是梦见一位手持风灯踽踽而行的画僧,和那个“三人舞”中不断复现的“主飞天” ;画僧日常化的行走和“主飞天”超常性的扶摇,似乎都成为吴铭忘我工作的动力之源,他带着助手水雯为保护敦煌文物而废寝忘食。作为剧中第三号人物的水雯,不仅是基于芭蕾艺术形式规律的考虑(否则在念予远去后的整个第二幕,将失去‘双人舞’这一重要表现手段) ,而且也符合我们对现实题材表现时应遵循的“细节真实”要求;第二幕的二场和三场,编导让现实的吴铭超越了现实——他先是被画僧的虚像引领、继而承继了画僧的心性。这时我们才明白,那位踽踽而行的画僧其实是吴铭对自己内心的倾听,编导想让观众明白那位古代的画僧就是当下的吴铭,想让观众明白我们古国文明的薪火相传是因为从来都有这样倾听着“祖先脚步声”的“民族脊梁” ……念予再次回到敦煌已是舞剧《敦煌》的“尾声”了——她的记忆与敦煌的现实叠加,她在最初的追随“飞天”时遇到了吴铭,而献身敦煌保护事业的吴铭成了她人生“现在时态”中的“飞天”!在这个意义上,舞剧《敦煌》似乎成了念予为我们讲述的一个故事——念予兼具了讲述者和剧中人的双重身份。
大型芭蕾舞剧《敦煌》剧照
舞剧《敦煌》作为一部成功舞剧的
四大艺术特征
女主角念予作为舞剧《敦煌》的首席人物、同时又作为这一舞剧故事的讲述者,是该剧第一个鲜明的艺术特征。我们有不少舞剧都设置了“讲述者” ,有设置“老者”讲述远古,也有设置“后生”缅怀先贤,但都未能如念予这样——舞剧《敦煌》是因她的“念想”而启程,因她切身的投入而展开,最后又因她的追忆而生“崇敬”之感……这使得念予在讲述一个完美的故事时,也成了一个完美的故事讲述者。舞剧《敦煌》第二个鲜明的艺术特征,是以“主飞天” (包括构成“主飞天”整体造意的“三人舞” )来建构舞剧结构的“形式感” 。这个“三人舞”仿佛舞剧形式建构的“主题动机” ,在它的复现、变异、演进中,强化了舞剧结构的“音乐性”特征,使这部舞剧不是“戏剧”的“舞蹈演绎” ,而真正体现出舞剧艺术的“本体性” 。
上述凸显着“主飞天”的“三人舞” ,在剧中还承担着一个重要使命,这便是沟通着现在时态的“敦煌人”和过去时态的“敦煌壁画” ( “画中人”以及“画中神” )。这使得“敦煌人”与“敦煌壁画”的时空转换自如妥帖,也使得二者在同一时空的合舞共蹈自然融洽。这一点对于舞剧《敦煌》的故事讲述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构成了该剧第三个鲜明的艺术特征。该剧这次打磨的成功,还体现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舞蹈语汇” 。我们知道,芭蕾是一种形式感很强的舞蹈范型。四百余年的历史建构,使它的“风格图式”在人体比例美和体动技能美的基础上得以稳固确立。对于这个“足尖上的敦煌” ,我真正关心的是编导会怎样用芭蕾的“风格图式”去整合敦煌的“壁画舞姿” ,而不无担心的则是,敦煌壁画中那些灵动的“香音神”(飞天)和妩媚的“伎乐菩萨”,会否在“开绷直”的图式中失去“S”形扭动的风韵?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芭蕾图式对于敦煌舞姿既非“整合”也非“结合”,而是“水乳交融”般的“融合” —— “主飞天”在该剧的语汇融合中是“点睛之笔”;而壁画造像中的美音鸟、天宫伎乐乃至供养人的舞蹈,都以不同的方式融合在芭蕾审美中,使人在慨叹这是一种“真正的芭蕾”之时,更赞叹这是一种“真正的中国芭蕾”。由舞蹈语汇精心推敲的这一方面,成为该剧第四个、可以说也是最关键的艺术特征。
大型芭蕾舞剧《敦煌》剧照
从《红色娘子军》《祝福》
《大红灯笼高高挂》到《敦煌》的
“芭蕾中国学派”
对于“中国芭蕾” 、或者说对于“芭蕾中国学派”的建设,中央芭蕾舞团一直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 1964年,在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之际创排《红色娘子军》后,历任中央芭蕾舞团的领导都高度重视通过作品来打造“品牌” ,通过作品的不断求索来汇聚“学派” ……新时期以来,首位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的,是舞剧《红色娘子军》最重要的舞蹈编导李承祥。在他的任期中,借“鲁迅先生诞辰百年” (1981年)的契机,推出了由蒋祖慧(也是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创排的舞剧《祝福》,开始了中国芭蕾“心理结构舞剧”的新历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赵汝衡接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在她任期内的新世纪初,推出了由张艺谋担任编剧和导演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舞剧的编舞先后由王新鹏、王媛媛担任,经两年修改、打磨而成为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芭蕾”。现任团长冯英, 2009年才从“芭蕾大师”任上上岗,上岗以来开拓了每年一届的“创意工作坊”,至今已亮相“八届”,使许多优秀的舞者向编导转型。对于大型舞剧的创作,冯英一直认同“现实题材”的创作,比如当下的《敦煌》和此前的《鹤魂》。冯英工作很努力,但我一直担心、或者说一直期盼的是,在她的任期内能有一部怎样的舞剧来支撑?在看了经过费波创排并用了近一年时间精心打磨的舞剧《敦煌》,我的担心得以释然,期盼也大有所得……写作至此,耳边似乎响起“我送你一朵玫瑰花,我要好好地谢谢你……”的歌吟;由此而联想到,舞剧《敦煌》是冯英在任期内送给我们的一朵“芭蕾玫瑰”,也是她和她的团队为世界芭蕾送上的“一朵足尖上的‘敦煌’”!
(本文图片摄影:时任)
原创: 于平 中国艺术报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