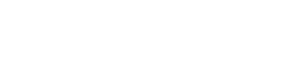摘要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史上,乔托素来享有“近代绘画之父”的盛誉,然而这不过是以瓦萨里为代表的艺术史书写建构出来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位置。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肇始也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这一努力到13世纪末开始汇聚为具有意大利特色的“方言”,奇马布埃、杜乔和乔托则是同时代的三位风格大师,是他们共同创立了文艺复兴艺术的“开端”。
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起源”,自16世纪瓦萨里(Vasari)将乔托(Giotto)置于“创始之父”的位置以后,这一说法相沿成习已经成为一个传统。然而,瓦萨里的艺术家传记是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写作,是通过一套以佛罗伦萨画派作为标准的艺术话语和历史叙事框架来对地区多样化的国别艺术进行编码的文化实践。也就是说,乔托作为“创始之父”的位置首先是话语实践的结果,在今天,要启动对创始位置的重新思考,当然可以有很多路径,但有一条路径必不可少,那就是将创始问题重置于历史场景中进行考察。可如何进入历史场景呢?就艺术史的角度而言,有一个主题类型可以为我们的进入提供通道,那就是圣母子像中流传最广的“指路圣母图”。
一、“指路圣母图”与拜占庭风格
所谓“指路圣母图”(Virgin Hodegetria),就是圣母一手(一般为左手)抱着圣子,另一手指向圣子,意思是:“道成肉身”,这就是基督所要行的“道”,也是他将以十字架上的受难指示给众人所当行的“道”、当信的“真理”和当践行的“生命”;圣子则一手拿着经卷,一手做出祝福的姿势。大部分时候,圣母子的两侧还有天使或圣徒相伴。
传说中,第一件指路圣母像是由福音书作者路加绘制的。据6世纪拜占庭的一位编年史家记述:5世纪拜占庭帝国摄政女王艾丽娅·普尔切莉亚(Aelia Pulcheria,398—453)统治期间,主持修建了三座敬献给圣母的圣殿,其中有两座供奉的是圣母的遗物,第三座为霍德贡修道院(Hodegon Monastery),其中供奉的是女王从巴勒斯坦请回来的、据传出自路加之手的一件双面板上画,一面画的是指路圣母,另一面画的是基督上十字架。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路加画圣母像的故事可能是根据一幅已经存在的圣母肖像画附会出来的。不过,圣像捣毁运动之后,为重新点燃人们对圣像的热情,这个传说流传甚广,霍德贡修道院的圣母像被认为是路加所绘圣母肖像的标准版本,“Virgin Hodegetria”(指路圣母)也由此而得名。[1]根据毕塞拉·V·潘切瓦(Bissera V. Pentcheva)的研究,以前君士坦丁堡的宗教游行是抬着帝国守护神圣母的圣遗物,圣像捣毁运动结束后,霍德贡修道院的指路圣母像成为游行队伍的中心,其摹本也开始出现在钱币、教堂的马赛克装饰中。[2]但不幸的是,霍德贡修道院的原作在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的时候遗失了。
实际上,因主题的不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圣母像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比如“哺乳圣母”“谦卑圣母”“慈悲圣母”“领报圣母”等,“指路圣母”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但也是流传最广的类型,它在艺术史中更为人熟知的提法叫“圣母子像”。圣母子像又有半身像和全身像两个亚类型。前者是半身像圣母抱着圣子,后者是全身像圣母抱着圣子坐在宝座上,所以又叫“宝座圣母”。两种类型都产生于拜占庭,其中半身像多用于私人祀拜,全身像(时常有骑士圣徒或天使在一起)多用于公共场景来展示帝国的权力和荣耀。它们在中世纪的时候传入西方,是西方圣母子像的源头,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中时常提及的拜占庭风格。
然而,在许许多多的艺术史家那里,“拜占庭风格”是一个意义含混不清的总体概念,例如就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拜占庭风格而言,它的源头除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本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源头,就是十字军时代由拉丁十字军控制的黎凡特地区,这个地区的圣母像生产虽然图式基本遵循拜占庭传统,但在动作设计和形象装饰上却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更新的艺术史研究倾向于给它一个新的名称:“十字军艺术”[3](Crusader Art)。
希腊工匠,《圣母子镶嵌画》,13世纪初,镶嵌画,44.6厘米×33厘米,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
拜占庭工匠,《宝座上的圣母子和供养人》,10世纪中叶,马赛克,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
例如圣母子像,在拜占庭传统中,圣母形象及其衣饰通常没有金线装饰,而到十字军艺术中,金线装饰以及金色基底成为惯例,据研究“十字军艺术”著称的艺术史家贾罗斯拉夫·弗尔达(Jaroslav Folda)描述说:
与将圣母视作上帝之母和天后(升到天上并被加冕的王后)的精神意义的全新理解相对应,十字军艺术家引入了跟拜占庭圣像画家不同的金线来描绘圣母的形象。结果,在这些新圣像中,圣母子都放射出神圣的光。这意味着,在那些为近东十字军及其他西方委托人创作的艺术家手中,拜占庭的圣母作为“Theotokos”即耶稣生母的观念,变成了光芒四射的神圣的上帝之母,她以拜占庭“指路圣母”的形象抱着神圣的人子,她对耶稣的神态象征地指示了救赎之路。[4]
具体到拜占庭和十字军艺术对意大利绘画的影响,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实际上,这一影响的发生有着各种各样的途径,例如外交赠礼、朝圣、贸易、战争等。在意大利本岛,还有中世纪早期到盛期存留在罗马、西西里、拉文纳、威尼斯等地教堂的马赛克,它们都是拜占庭风格,有一些其实就是拜占庭或希腊工匠亲自制作的。另外,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战争后,大量拜占庭和希腊画师来到意大利,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进行创作,指路圣母图也在这样的艺术交流中传入意大利。弗尔达说:
通过商业、旅行、朝圣、艺术交流、外交赠礼等手段,以及地中海两岸艺术家的往来(尽管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和十字军时不时从意大利跨过地中海到达拜占庭及十字军王国并从那些地方返回的人员流动,拜占庭传统的圣像画和十字军对这一传统的创新、改造与丰富被传播到西方。在重要的商业和艺术中心,如比萨、锡耶纳、卢卡、佛罗伦萨等,中意大利板上画画家同时挪用拜占庭和拜占庭化的形象:一方面是没有金线装饰的传统拜占庭指路圣母形象;另一方面是十字军创新的指路圣母形象,宝座上的或半身像的圣母在金色底子上因神圣的光而光辉四射。而且,在热情地挪用新形象的同时,中意大利的艺术家还渐渐地加以改变,使其圣母形象与拜占庭和十字军的原型有了本质的不同。[5]
十字军艺术在传统的黎凡特地区存留甚少,但在埃及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St. Catherine Monastery),保存有丰富的12、13世纪十字军艺术家绘制的圣像,其中包括指路圣母像,它们虽然看起来仍是十足的拜占庭风格,但也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偏离了拜占庭传统。[6]例如现存于圣凯瑟琳修道院的一幅便携式的指路圣母镶嵌画:在早期的拜占庭传统中,指路圣母像一般是圣母正面抱着圣子,圣子手握经卷,而在这里,圣母虽然仍是正面,但头部向圣子方向倾斜,圣子手中的经卷有一端支撑在膝上,背景则是十分风格化的装饰图案。整个作品手法极为精细,拜占庭式的线条在此不再只是为表现抽象的精神,而且在视觉上构建了一种优雅的风格,圣母身上用金线装饰的外袍强化了人子之母的神性在场,头顶的光晕和头巾的放射状纹饰既是神圣性的可见象征(光晕两侧的字符“ΜΡ ΘΥ”为“上帝之母”的希腊语缩写,进一步明确了圣母神性和人性的统一),也在视觉上框定了圣母瘦削的脸部,而其凝视又略带忧伤的眼神就像是对观看的聚焦。这一切在正统的拜占庭风格中是见不到的。
这种半身像的指路圣母后来在意大利早期的祭坛画中是最早出现也流传最广的一个标准范式,13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画家都画过这个题材。比萨的贝尔林基埃罗·贝尔林基埃里(Berlinghiero Berlinghieri,活跃期约1228—1236)可能是最早画这种圣母像的意大利画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一件被明确归于他名下的《圣母子》(约1230),其风格与后来的祭坛画相差无二。在那里,金色基底的运用、圣母头部向圣子的倾斜、圣子头上的光晕以内嵌的十字形制造的受难语义象征,这些都是十字军艺术的手法,但圣母子之间的交流意向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明确,圣子的祝福手势与圣母的“指路”手势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呼应,这一呼应的意义再借着圣母的目光传达给观者。
至于全身像的指路圣母,依传统更喜欢称它为“宝座上的圣母子”(Maestà),因为它总是呈现为全身像的圣母抱着圣子坐在宝座上,这个宝座又称“智慧宝座”(Throne of Wisdom)。在经典的拜占庭—十字军艺术传统中,这种宝座圣母总是跟王权联系在一起,例如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有一件大约绘制于6世纪的宝座圣母,是这座皇家修道院早期绘画的杰作,其构图要素是按照皇家要求配置的:圣母正面抱着圣子坐在用宝石装饰的宝座上,两侧是两位武士圣徒,后面两个手持权杖的天使长抬头看着天上,在那里,来自上帝之手的光束正降临在圣母的身上。三组人物的形态和表情依照各自的角色进行设定:圣母略显冷淡的目光与她的神性相匹配,武士圣徒直立僵硬的姿态与他们的职责相匹配,而两位天使长“透明的光晕、脸部和着装,飘逸的印象式笔触显示了早期古典的样式,具有一种与他们非形体的特性相匹配的空灵品质”。[7]
宝座圣母在拜占庭的教堂镶嵌画中也出现过。例如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西南门入口上方半月拱中的马赛克,直座式宝座上,圣母抱着圣子,两边是两位供养人,一个是君士坦丁一世即创建君士坦丁堡城的君士坦丁大帝,他手捧城市的模型敬献给圣母,另一个是修建圣索菲亚教堂的查士丁尼一世,所以他手上捧着教堂的模型敬献给圣母。
贝尔林基埃罗·贝尔林基埃里,《圣母子》,约1230年,板上坦培拉,76.2厘米×49.5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拜占庭画师,《宝座上的圣母子、圣徒和天使》,6世纪末,板上蜡画,68.5厘米×49.7厘米,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
就像在这里看到的,与王权相关的这种圣母和圣子都是正面朝向观者,母子之间没有交流。然而到十字军艺术中,宝座圣母变得形式多样。仅宝座的形态就出现了竖琴式、直座式和圆座式。圣母子也放弃了那种僵直的正面姿势,母子之间开始有了互动式的交流。
佚名画家,《卡恩圣母》,约1250/1275年,板上坦培拉,124.8厘米×70.8厘米,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佚名画家,《梅隆圣母》,约1260/1280年,亚麻布板上坦培拉,82.4厘米×50.1厘米,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有两件拜占庭风格的宝座圣母:一件是美国银行家和收藏家奥托·赫尔曼·卡恩(Otto Hermann Kahn,1867—1934)的家族捐赠的,所以现在叫“卡恩圣母”;另一件是美国银行家和收藏家安德鲁·威廉·梅隆(Andrew William Mellon,1855—1937)的家族捐赠的,所以现在叫“梅隆圣母”。两件作品因风格上的许多共同点而时常被人放在一起讨论。
有点奇怪的是,两件作品20世纪初几乎同时出现在马德里的艺术品市场,然后流入不同藏家之手,几经辗转,最后都到了美国,并进入同一个美术馆。至于它们的作者归属和最初的功能,艺术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目前比较被人接受的意见是:它们可能出自在君士坦丁堡接受过训练的两位希腊画家之手。[8]
两幅画都是拜占庭指路圣母的传统,身穿连衣裙和外袍的圣母坐在精心制作且带有镂空装饰的木制宝座上——但宝座形态不同——她的左臂支撑着圣子,俨然是圣子的宝座,圣子双脚放在母亲的左膝,手上拿着经卷。在“卡恩圣母”中,圣子身子转向母亲,并对她做祝福的手势;而在“梅隆圣母”中,圣子俨然天上的王,正面端坐,他眼睛看着观者方向,并做出祝福的手势。在两幅画的顶端,宝座两侧各有一个圆形的天使半身像,天使的服饰属典型的拜占庭皇室风格。
“宝座圣母”表达的是对“天后”圣母的崇拜。所以拜占庭宫廷总是将它和王权的彰显联系在一起。而十字军时代在保留拜占庭元素的同时,图像的配置变得更为丰富,例如上面的两件作品,圣母有着标配性的服饰:蓝色或红色外袍、蓝色内套、红色的鞋子、头巾、金色的光晕,它们都辅以装饰性的金线和金色底子。圣子头上的光晕都内嵌有一个象征牺牲的十字形。另外还有拿着法杖的天使(这也是典型的拜占庭宫廷元素)伴随两侧。
在意大利,“宝座圣母”至少在12世纪的时候就以雕塑的形式出现了,但真正流行是在13世纪祭坛画兴起以后,托斯卡纳地区的卢卡、比萨、锡耶纳、佛罗伦萨等城市是生产这种圣母像的中心。[9]
卢卡和比萨是托斯卡纳地区相邻的两个城市,10至11世纪的时候,它们一个靠着丝绸贸易、一个靠着强大的海上力量和东方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富有的城市。13世纪的时候,两个城市涌现了许多画家,历史上称之为卢卡画派和比萨画派。[10]在他们为数不多的作品留存中,有两件保存完好的“指路圣母”堪称时代的杰作。
有关这件作品的收藏史,苏联艺术史家维克多·拉萨列夫(Victor Lasareff,1897—1976)曾有一个简短的描述,称它可能早在13世纪的时候就被教皇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个俄罗斯大公,几经流转后在1925年为莫斯科艺术博物馆(今普希金美术馆)获得。[11]但拉萨列夫称它是一幅“圣像画”的说法遭到学者们的反对,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和弗尔达都认为它是一幅祭坛画,因为它的大尺幅、方形结构以及“宝座圣母”主题正是这个时期中意大利的祭坛画最为流行的样式。当然,我们在此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到它对十字军的“指路圣母像”的吸收:竖琴式的座背、手执法杖的带翼天使、深蓝和红色为主色调的服饰配置、红色的鞋子等。然而,至少有两个细节显示了艺术家非凡的“改变”:第一,圣母头上的光晕用了两圈极具立体感的小三角形来制造光辉四射的效果;第二,圣母穿着红色鞋子的双脚是“踩”在踏板上,而不是像拜占庭和十字军艺术那样“悬”在板子上。这两点,还有座背的描画,都彰显了一种本土化的、独特的图像冲动,那就是对“形体感”的追求。
比萨画家,《普希金圣母》,13世纪下半叶,板上坦培拉,173厘米×84厘米,莫斯科普希金美术馆藏
类似的,现藏德国科隆瓦拉夫—里哈尔茨美术馆(Wallraf-Richartz Museum)的一件卢卡画家创作的“宝座圣母”也有非凡的表现。圣母头上的王冠,椅背柱子上的装饰图案,圣母外袍上精美而沉着的织花,自然而流畅的褶纹,以及透过裙褶的变化表现出来的圣母的双膝,艺术家在这些地方都显露了某种自然主义冲动。
当然,旧式的拜占庭传统在意大利也有传承。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The Uffizi Gallery)有一件被归为13世纪30年代的“圣母子”就是这个类型:风格化的宝座上,圣母将圣子抱在怀里,圣母头上的光晕以雕塑形态伸出画板以外,两个天使在画板顶部的两侧;圣母和圣子两个形象都是正面朝向观者,眼睛凝视着画外的远方,圣子一手握着经卷,一手以王者的姿态做出祝福。但画作中圣母脚下以“非科学”的缩短法表现的踏板却是全新的本土语言,圣母裙子上如星星般散布的金色圆点和风格化的褶皱也显示了艺术家寻求改变的冲动。
虽然早期作品中只有很小部分得以留存至今,但仅有的遗存明确地显示,意大利艺术家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尝试对拜占庭风格的改造。尤其在13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修会教堂的大量兴建,对祭坛画的需求急剧增加,而修会对祭坛画的功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要求;进而,修会之间的竞争又使得所要求的内容及其满足方式趋于多样化;就这样,祭坛画从刚开始作为圣像画的单一祀拜功能渐渐扩展到多功能的并置,其框架形制、题材内容和图像配置的不断变化就与功能的多样化有着直接关系。例如指路圣母图,至少从13世纪60年代开始,来自修会的大型委托渐渐多了起来,少数艺术家在因循拜占庭传统的同时,也努力为图像内容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佛罗伦萨的科波·迪·马可瓦尔多(Coppo di Marcovaldo,约1225—1276)和锡耶纳的圭多(Guido da Siena,约1230—1290)就是那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物。
1260年,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在锡耶纳的蒙塔佩蒂展开激战,锡耶纳人以寡敌众取得胜利。战役中,佛罗伦萨军队的一位持盾侍从兵被锡耶纳人俘虏关进监狱,他就是科波·迪·马可瓦尔多。锡耶纳一家新起的修会“圣母忠仆会”(Servite Order)听到消息后,从中斡旋把科波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条件是他必须利用特长为锡耶纳服务。忠仆会的第一件委托是要画家为修会在锡耶纳到罗马的朝圣之路上新修的教堂画一幅祭坛画。这件作品在艺术史上流行的名称叫“Madonna del Bordone”。关于这个名称的起源,一种说法是因为这幅画曾经安放在一个名叫“Bordoni”的家族礼拜堂,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叫法是因为朝圣者喜欢把手杖(pilgrim’s staff,意大利语bordone)放在画作下面的圣坛上。[12]
佛罗伦萨佚名画家,《宝座圣母和天使》,约1230年,板上坦培拉,119.5厘米×61厘米,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藏
卢卡画家,《宝座上的圣母子》,约1260年,布上坦培拉,104厘米×63厘米,德国科隆瓦拉夫—里哈尔茨美术馆藏
科波·迪·马可瓦尔多,《手杖圣母》,1261年,板上坦培拉,225厘米×125厘米,锡耶纳忠仆会圣母玛利亚教堂
锡耶纳的圭多,《宝座上的圣母子》,约1270年,板上坦培拉,283厘米×194厘米,锡耶纳市政厅藏
《手杖圣母》是蒙塔佩蒂战役后锡耶纳人委托的第一件圣母像。圣母抱着圣子端坐在座椅上,七弦琴一样的座椅靠背,穿着拜占庭宫廷服装的天使,绣有纹饰的红鞋,钻石图案装饰的脚垫,用金线装饰的衣袍,如此种种表明了作品对拜占庭风格的继承。但圣母不是正面面对观者,而是身子略微左转“斜坐”在王座上,圣子也不是正面坐在母亲双膝上,而是侧身由母亲抱着,他一手拿着经卷,另一手伸向母亲的头巾并做出祝福手势;圣母眼睛看着观者,头偏向圣子,似乎在迎合后者的目光,整个画面构成了极具人性化的交流场景。因此,虽然还是拜占庭画风的金色基底和线描技法,但圣母富于造型感的姿势和裙褶、圣母子之间人性化的神态交流已经为画面注入了新的精神,就像斯达布勒宾评论的:“他的天才就是把他自认为继承的艺术图式——意大利的和拜占庭的——加以变形,以至于人们常常很难确定他的出处和他的创新。”[13]
受到科波的影响,锡耶纳的圭多也采用圣母侧身的方式来寻求画面的人性化效果,他有一件“宝座圣母”是为锡耶纳多明我会的教堂绘制的,原作现藏在锡耶纳市政厅,多明我会修道院教堂里展示的是复制品。这是一件挂屏,但原作似乎遭到解体,幸存的饰板分散在各地的美术馆,所以对于其原初的图像构成,艺术史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相关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14]
与13世纪流行的拜占庭风格的“宝座圣母”相比,这件作品最显著的一个不同就是对金色基底和宝座关系的处理,即通过让宝座与图画平面呈一定角度而使两者发生分离,这种做法在比萨画家那里有过初步实验,但圭多走得更为激进,他明显把基底改造成了“背景”,由此在画面中制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空间感”。
对意大利绘画而言,科波和圭多的宝座圣母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很快地,受他们的启发,新一代艺术家将在他们的基础上对图式做进一步的完善,并发展出完全本土化的语言。13世纪80年代,意大利祭坛画开始了历史的新阶段,其标志恰恰就是几件宝座上的指路圣母图。
二、归属之争
在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2号展厅,展示有三件大型的“宝座圣母”,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意大利最杰出的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即杜乔的《卢切莱圣母》(Rucellai Madonna)、奇马布埃的《圣三一圣母》(Maestà di Santa Trìnita)和乔托的《万圣圣母》(Madonna di Ognissanti)。三件作品创作的时间前后相距不过20余年,巧合的是,三者的委托都出自佛罗伦萨,且都是以宝座上的“指路圣母”为题材。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意大利祭坛画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方言”和风格。
奇马布埃,《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圣母子》,约1283—1284年,板上坦培拉,69厘米×51厘米,佛罗伦萨圣维尔蒂亚娜美术馆藏
杜乔·迪·博尼塞尼亚,《克雷沃勒圣母子》,1283—1284年,板上坦培拉,89厘米×60厘米,锡耶纳大教堂博物馆藏
三件作品中,杜乔的《卢切莱圣母》因历史原因和奇马布埃发生了复杂的纠葛。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两位艺术家开始,他们在许多方面的确像是了解对方的一面镜子。
奇马布埃大约出生于1240年,杜乔大约出生于1255年。两人早期成为画家的经历都晦暗不明,但无疑都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比如13世纪60至70年代托斯卡纳的画家对圣像画的改造。两人的圣母像创作大约都开始于1280年代初,且明显属于已经意大利化的拜占庭风格。现今人们在讨论这些作品的时候,喜欢将它们放在一起相互参照,甚至把创作时间也归在同一时期。
例如两人在1283年左右创作的指路圣母半身像。奇马布埃的作品现藏在佛罗伦萨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Castelfiorentino)的圣维尔蒂亚娜美术馆(Museo di Santa Verdiana),所以称为“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圣母子”;杜乔的作品原先是为锡耶纳小镇蒙特佩西尼(Montepescini)奥古斯丁会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绘制的,后随修会一起转到克雷沃勒(Crevole)的圣塞西莉亚教堂(Pieve di Santa Cecilia),所以称为“克雷沃勒圣母子”。
两件作品的风格几乎一样,以至于艺术史家一度把奇马布埃的作品归在杜乔的名下。但仔细比较会发现,奇马布埃的圣母笔法表现较为生硬,例如鼻子到前额和鼻子到嘴的过渡过于突兀,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太宽,使得脸部结构不够紧凑。圣子的表情和姿势刻画也几近失控。相比之下,杜乔的技法要完美得多:脸没有那么宽,描绘五官的线条更为流畅,拜占庭式的金线装饰和衣褶处理更为自然,圣子与母亲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更加人性化。
奇马布埃,《忠仆圣母堂的宝座圣母》,约1280—1285年,板上坦培拉,218厘米×118厘米,博洛尼亚忠仆圣母堂
杜乔·迪·博尼塞尼亚,《瓜里诺圣母》,约1280—1283年,板上坦培拉,157厘米×86厘米,都灵萨包达美术馆藏
可以拿来对比的还有更早的两件指路圣母全身像,艺术史家通过风格对比推测,它们可能属于艺术家走向风格成熟前的作品。奇马布埃的作品现保存在博洛尼亚的忠仆圣母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dei Servi),杜乔的作品以前是实业家、收藏家里卡尔多·瓜里诺(Riccardo Gualino,1879—1964)的私人藏品,后来卖给了都林萨包达美术馆(Galleria Sabauda)。有趣的是,20世纪初杜乔的这件作品正式公诸于世的时候,曾一度被归在奇马布埃的名下,后来才被确认是杜乔的手笔,其创作年代推测在《卢切莱圣母》之前,从圣母脸部线条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来它属于艺术家较早期的作品。至于奇马布埃的圣母图,其作者归属也存在异议,但主流意见多倾向于是由奇马布埃本人或他的作坊一起完成的,完成时间可能比卢浮宫的“宝座圣母”晚,但比圣三一教堂的“宝座圣母”早。
杜乔的作品直接就是方形板,奇马布埃的作品虽然带有尖顶板,但采用的是方形构图,宝座后面的天使不是飞行在顶端,而是立于宝座后面,这与杜乔的处理是一样的。两件作品都是拜占庭风格的竖琴式宝座,但奇马布埃的宝座与图画平面是平行的,而杜乔的宝座与图画平面成一定角度。两件作品中圣母和圣子的位置及姿势正好相反,但关系配置近乎一样,就像是同一个画家画的双联画。这种相似很容易让人想到是其中的一个模仿了另一个,但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形是:它们有共同的源头。佛罗伦萨艺术史家卢奇亚诺·贝洛西(Luciano Bellosi)是研究奇马布埃和杜乔的专家,他就持有这种观点,认为两件作品有可能是追随了科波为圣母忠仆会绘制的宝座圣母祭坛画。[15]
上面两组作品都算不上出色,其作者归属和确切的创作时间也都难以确定,但它们之间如此之相似,以至于艺术史家在作者归属上多次出现张冠李戴。对于这种相似性,现今的艺术史家给出了一个解释:两位艺术家之间是师徒关系或至少是一个受到了另一个的影响,确切地说,是年轻的杜乔受到了年长的奇马布埃的影响。然而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这种猜测或假设并不可靠:年轻的艺术家受到年长的艺术家的影响,这也许是历史中的常态,但反向的影响同样是历史中的常态。支持奇马布埃影响杜乔的艺术史家还经常用风格分析来讨论杜乔是如何改进或完善老师的不足,但这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的观点,因为艺术史中后来者比原型退步的情形同样是一种常态。
为什么艺术史家在影响问题上会出现如此顽固的单向设定呢?这跟另一件作品的归属纠纷有关,跟艺术史家的历史执念有关。引起归属纠纷的作品就是杜乔于1285年在佛罗伦萨为敬奉圣母的“赞歌兄弟会”(Compagnia dei Laudesi)创作的《卢切莱圣母》。
赞歌兄弟会是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最有影响力的市民宗教组织,它是多明我会的殉教者、维罗纳的圣彼得于1245年在佛罗伦萨创立的。兄弟会平时经常聚在一起唱赞美歌礼赞基督和圣母,在特别的纪念日或节庆日的夜晚还会举着蜡烛在教堂列队礼赞和吟唱。[16]
赞歌兄弟会在新圣母马利亚教堂有一个献给教皇大格里高利(Saint Gregory the Great,约540—604)的礼拜堂,有学者认为杜乔的画是受这个礼拜堂委托的。[17]但格里高利礼拜堂在1336年被转给了巴尔迪家族,作品为何进了卢切莱家族的礼拜堂,已经无从知晓。卢奇亚诺·贝洛西(Luciano Bellosi)认为,杜乔的作品虽然是赞歌兄弟会出资委托,但它并非兄弟会的资产,也不是为兄弟会的礼拜堂订制的,考虑到该作品巨大的尺幅,以及新圣母马利亚教堂作为当时佛罗伦萨最大的教堂(新的圣十字教堂和圣母百花大教堂分别要到1295和1296年才开始扩建),作品有可能是为教堂里面最重要的视觉区域——圣坛前屏——制作的,不久之后,前屏上方还将悬挂着乔托绘制的巨型十字架。[18]但贝洛西的说法也只是猜测。
16世纪初,佛罗伦萨僧侣作家弗朗切斯科 · 阿尔贝蒂尼(Francesco Albertini)在他的“回忆录”中首次把《卢切莱圣母》归在奇马布埃的名下,说奇马布埃在新圣母马利亚教堂有一件“巨型祭坛画紧挨着菲利波· 布鲁内莱斯基的优美的十字架”。[19]阿尔贝蒂尼提到的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木制十字架(大约制作于1410—1415年)当时可能是挂在唱诗席左边的冈迪(Gondi)礼拜堂和巴尔迪(Bardi)礼拜堂之间(1572年被移到冈迪礼拜堂,现在还在那里)。阿尔贝蒂尼关于“奇马布埃祭坛画”的位置描述并不具体,但他给出的作者归属为后世所接受,瓦萨里就沿袭旧说,称这件祭坛画是奇马布埃最杰出的作品。在有关奇马布埃的传记中,瓦萨里还根据坊间逸闻编写了一个作品的安装“盛况”:
接着,他(奇马布埃——引者注)又为圣马利亚·诺威拉教堂作了一幅木板画《圣母》,悬挂在卢切拉伊礼拜堂和维尼奥的巴尔迪小礼拜堂之间的墙壁上。画中人物的尺寸要比以往所有绘画中的人像大,虽然画中的天使仍旧是拜占庭风格的,但从一些方面来看,奇马布埃已开始尝试现代的艺术技巧和方法。当时的人因为很少看到如此优美的作品,故而对这幅画非常推崇,他们把这幅画从奇马布埃的寓所送往教堂,一路上,吹号打鼓,举行盛大的游行仪式,奇马布埃本人自然也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和丰厚的报酬。[20]
瓦萨里1568年记述的作品位置是卢切莱礼拜堂和巴尔迪礼拜堂之间的墙上,大约此后不久,作品被移到卢切莱礼拜堂里面的圣坛上,直到1948年才被转到乌菲齐。“卢切莱圣母”这个名称也是由此得来。
1790年,新圣母马利亚修道院的一位档案管理员发现了1285年赞歌兄弟会委托杜乔的合同,第一次通过证据确认“卢切莱圣母”是杜乔的作品。但这一发现并未引起艺术史家的注意,19世纪中期,英国人约瑟夫 ·亚切 ·科威(Joseph Archer Crowe,1825—1896)和意大利人乔凡尼 · 巴蒂斯塔 ·卡瓦尔卡塞莱(Giovanni Battista Cavalcaselle,1819—1897)在他们合著的《意大利艺术史新编》中仍把“卢切莱圣母”归在奇马布埃的名下。[21]1888年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离异者约瑟夫·斯特尔齐戈夫斯基(Josef Strzygowski)在《奇马布埃与罗马》一书中仍沿用旧说,视《卢切莱圣母》为奇马布埃的代表作,但他惊讶地发现《卢切莱圣母》和锡耶纳的圭多的《圣多明我宝座圣母》之间的“家族相似甚至多于和奇马布埃本人的圣三一圣母之间的相似”,所以奇马布埃必定是受到了圭多的影响。[22]
然而,就在斯特尔齐戈夫斯基的论证发表一年以后,即1889年,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弗朗茨·维克霍夫(Franz Wickhoff)在一篇讨论锡耶纳的圭多的论文中通过风格比较和文献证据正式将《卢切莱圣母》归在杜乔名下,一直以来的错误终于得到纠正。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纠正引发了19世纪末艺术史家对瓦萨里制造的奇马布埃神话的全面质疑,极端怀疑论者甚至认为,瓦萨里对佛罗伦萨人迎接“卢切莱圣母”的盛况描写是受到了锡耶纳史家记述1311年锡耶纳人迎接杜乔为大教堂高坛创作的《宝座上的圣母子》的场景的启发;[23]而另一些艺术史家基于各种理由或动机又重新想象了一个“师徒关系”来延续奇马布埃的“英雄神话”:杜乔很有可能在奇马布埃那里学习过,至少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但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依照所谓的风格比较获得的,并没有文献或相关的史实支撑。
艺术史家如此热衷于从风格比较中推出单向影响的结论跟瓦萨里制造的现代绘画的“起源”神话有关,在那里,乔托被设定为文艺复兴绘画之“开端”,奇马布埃作为乔托的老师是这个开端的“引子”。奇马布埃自己的老师呢?当然不是他曾经请教过的希腊画师,而是“自然”。从“发现自然”到“再现自然”,再到“超越自然”,这就是瓦萨里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建立的叙事主线。而居于叙事首尾的都是佛罗伦萨人:从奇马布埃和乔托开始,到米开朗基罗收尾,一个看似完整实际上封闭的意识形态叙事由此建立起来。瓦萨里的传记细节有许多后来被质疑和被纠正,但他的叙事框架始终维系着。而现在,起始被确立为“现代的艺术技巧和方法”的尝试之作居然不是出自奇马布埃,历史的“黑洞”顿时让已经正典化的艺术史陷入了慌乱,艺术史家于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修补工作。首先是重新定位奇马布埃的作品,就像海登·B·J·马金尼斯(Hayden B. J. Maginnis)说的:“如同自然界一样,学术界也惧怕真空,于是奇马布埃的‘圣三一圣母’(瓦萨里在传记第二版仅仅提了一下)取代‘卢切莱圣母’成为宣告绘画重生的作品。这样,瓦萨里的幻象得到了拯救,而杜乔的木板画被降级到次要位置,且被牢牢锁定为锡耶纳画派简朴又保守的‘抒情式’描写。”[24]其次就是通过师徒关系的想象来让“起源”神话归位到原点。
例如,阿多尔夫·文图里(Adolfo Venturi)在卷帙浩繁的《意大利艺术史》中通过对杜乔的《卢切莱圣母》和奇马布埃现藏卢浮宫的“宝座圣母”的详细比较,认为前者显然追随了奇马布埃的风格:“奇马布埃创立典范,杜乔将之传播。因此真相与有些人想要证明的恰恰相反。奇马布埃……迷住了这位年轻的锡耶纳人,这种情况在各个时代伟大的大师当中时常会发生。”[25]相较之下,当代艺术史家的观点要温和一些,例如卢奇亚诺·贝洛西(Luciano Bellosi)就认为两位画家的关系可能比单纯的师徒关系更为复杂,他说:1280—1285年是奇马布埃威望达至顶峰的时期,意大利的许多城市都有他的创作和追随者,“总而言之,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画家在这个时期必定是‘叱咤画坛’,这一无可匹敌的光辉形象对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天才即锡耶纳的杜乔·迪·博尼塞尼亚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尽管锡耶纳和佛罗伦萨两个城市关系紧张。年轻的画家并不是学徒……他亲近奇马布埃是一种个人选择,作为一个有着远见、雄心勃勃、聪慧和心胸豁达的年轻人,他不愿满足于从师傅那里接受他已经熟悉的教诲,他想要获得更多。因而这是两个天才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有可能更多地是两个伟大的心灵、天生的画家之间热情奔放的对话,而不只是年轻人对长者的消极服从。”[26]
三、杜乔与奇马布埃之间
如同在文图里那里看到的,在对单向影响的确认中,人们时常把《卢切莱圣母》和奇马布埃的《卢浮宫圣母》放在一起来证明一个对另一个的影响。按瓦萨里的记述,后者是奇马布埃为比萨圣方济各教堂的一个圣坛绘制的,后来被移到教堂别的地方。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将其劫掠到法国,且一直没有归还,现展示在卢浮宫。影响比较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奇马布埃的《卢浮宫圣母》早于杜乔的《卢切莱圣母》,人们通过风格研究把《卢浮宫圣母》的创作时间回溯到1280年代初,最新的研究甚至把创作时间推到1265年比萨圣方济各教堂扩建的时候,虽然现有文献档案只能确认奇马布埃是1301年在比萨工作。[27]
不过,这两件作品之间的确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如果说是奇马布埃影响了杜乔——这种可能性更大——那这里表明了什么呢?不是单纯的“源头”和“衍生”的关系,而是不同图像冲动或“艺术意志”的表现,因为两位艺术家自身也是此前不同源头的汇流,这些源头就像一个又一个的冲动“碎片”,在这里经过融合形成更为系统、统一的图像表达,奇马布埃对空间的探索和杜乔对装饰性的偏爱,成为接下来的佛罗伦萨画派和锡耶纳画派所致力的两个方向。也就是说,奇马布埃对杜乔的影响是存在的,但不是唯一的,如同奇马布埃也是不同源头影响的结果一样。可以比较一下两件作品最具意义的相同和不同。
奇马布埃,《卢浮宫的宝座圣母》,约1280年,板上坦培拉,427厘米×280厘米,巴黎卢浮宫美术馆藏
杜乔·迪·博尼塞尼亚,《卢切莱圣母》,1285年,板上坦培拉,450厘米×290厘米,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藏
首先是框架。两件作品都有一个方形板加尖顶的框架,但杜乔的框架用了精美的细工制作,刻意强化了框架和画面的分离。重要的是,两者都对框架本身进行了装饰,相对于13世纪的祭坛画而言,这是十分现代的做法——13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的方济各像挂屏曾用装饰框来框定圣徒像——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画框”。但它的功能不只是装饰,更不只是为了在巨大的教堂空间来“框定”人们的视觉范围,因为在框架的板条上,艺术家绘制了一系列圆形半身像,并用精美的叶饰图带将它们分离开来。这些圆形像构成了中心文本的延展部分,其功能类似于14世纪多折板的侧板或饰板。在奇马布埃那里,一共有26个圆形像,尖顶上是基督像,基督两侧是四位天使,方形板四个角上打开经卷的四个形象可能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底边中间的五个形象是圣徒像,两个侧边剩下的十二个形象是十二门徒。而在杜乔那里,一共有30个圆形像:尖顶是救主基督,基督右边一直往下是十二门徒像,左边一直往下是十二位旧约的国王和先知像,底部的另外五位从左到右是: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圣多明我、圣奥古斯丁、圣泽诺比乌斯(佛罗伦萨的主保圣徒)和殉教者圣彼得。[28]所以,两件作品的圆形像不仅是中心板圣母所代表的教会的保护人,也是对“新约”(人子的爱的宗教)和“旧约”(天父的律法的宗教)的关系的说明,而底部的圣徒形象相当于是对修会信奉的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宣讲。以这种方式,“框架”被纳入图像的表意系统,成为作品不可分离的部分,这无疑是伟大的创新。
再看圣母的宝座。两件作品都再现了竖琴式的木制宝座,且都呈现为与图画平面成斜角的放置。杜乔再一次使用了细工装饰,与奇马布埃朴素、稳固但略显笨拙的特征相比,杜乔的宝座刻画得更为细致,宝座的形制更为优雅。尤其是,奇马布埃的宝座仍保留有十分传统的拜占庭风格,而杜乔“创造”了一个完全“现代”的宝座图像:他为宝座“安装”了一个哥特式靠背,一排圆弧形的拱顶,上面挂着一块缀满花饰的锦缎作为“幕布”。这当然已经不是单纯的装饰。如果说奇马布埃的宝座还重在传达“智慧宝座”的象征意义,那杜乔就是在这个象征性之上叠加了“视觉性”,更确切地说,是用视觉性来让象征性在意义的延宕中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比如它还代表着对天后圣母美德的赞美,代表着对天国圣境的想象。
还有宝座的摆置。两个宝座的斜角摆置在祭坛画中并非第一次出现,此前的比萨画家已经有过尝试。斜角摆置产生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效果:宝座和金色基底的分离,就是说,使基底变成了空间意义上的“背景”。所以我们看到,奇马布埃让天使站在宝座“后面”,而不再是漂浮在超现实的或“非空间”的存在境域,但奇马布埃的宝座前端紧贴着图画边沿,使得宝座前面的空间十分局促,给人感觉宝座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挤压。而在杜乔那里,宝座前面用台阶制造了一个空间纵深,使得宝座在空间中舒展自如,宝座和基底之间也形成了十分明确的“主题”/“背景”关系。
再看圣母子。两个人的圣母姿势十分相似,就像来自同一个拜占庭模板。但圣母服饰的表现迥然异趣,杜乔的圣母穿着拜占庭传统的红色和蓝色衣袍,但没有拜占庭的金线装饰,而是在圣母的头套和外袍右肩上各绘制了一颗星星,以作为对圣母美德的赞美;同时,外袍用金线镶边,从圣母的头顶蜿蜒滑过两颊,到胸前汇合,再穿过双膝,到下摆汇成金色飘带般的舞蹈,既完美地勾勒了圣母的形体,灵动的金色又在蓝色外袍上构成了一道奇幻的风景线。而在奇马布埃那里,这种象征和装饰都不存在,倒是那些断续的金线装饰让人想到拜占庭风格的拘谨。
两件作品中,圣子都是坐在圣母左膝上。在奇马布埃那里,圣母左手扶着圣子后背,右手扶着圣子右膝,圣子穿着罗马古代的服装,斗篷披在左肩,正面朝向观者,左手拿着象征律法的经书,右手做祝福的手势,一派尊贵的王者风范。而在杜乔那里,圣母左手穿过圣子腋下,像是护着幼小的孩子,圣子左手拽着像要滑脱的衣袍,转身看着右前方,右手做出祝福手势。显然,两位画家再现圣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个强调圣子的神性一面,另一个强调圣子的人性一面。
还有天使。奇马布埃的天使粗壮有力,6个天使站在宝座两侧扶着宝座的立柱,且都是正面看着观者方向,近乎拜占庭传统的变体。而杜乔的天使形态更加优美动人,他画的是六位赤脚天使,他们的服饰颜色代表着信(蓝色)、望(绿色)、爱(红色)三美德,其中底下两位天使半跪在地上,另外四位天使也是半蹲着,但不是蹲在地上,而是蹲在超现实的幻境,并且六位天使眼睛都向下或向上看着圣母子。天使形态的这一差异单纯从形式或风格方面是难以解释的,或者说,这一形态差异的后面其实隐含了两位艺术家对图像的“言述”行为的不同理解:奇马布埃的天使是圣母子及其王座的护卫者,是上帝的仆人;而杜乔的天使是祀拜者的目光内置,是祀拜行为的图像拟态,在那里,天使不是单一地护卫王座,而是要将王座升到天上,当然也有可能是将王座从天上落座到人世间,就是说,这个场景更像是祀拜的幻见或幻象。毫无疑问,在这个地方,奇马布埃再次稍逊一筹。
所以,就两位伟大的艺术家的这两件作品来说,杜乔的确是受到了奇马布埃的启发,但他对奇马布埃的巨大改造为锡耶纳画派的语言成熟奠定了基础。而接下来的乔托就将在这两位画家的基础上再做改造,从而为14世纪的佛罗伦萨画派奠定基础。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艺术史中,没有谁可以独当一面构成“起源”。
奇马布埃,《圣三一宝座圣母》,1280—1290年,板上坦培拉,385厘米×223厘米,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藏
乔托·迪·邦多内,《万圣圣母》,1306—1310年,板上坦培拉,325厘米×204厘米,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藏
现在可以看一下奇马布埃在乌菲齐的宝座圣母。同样地,作品确切的创作时间并不清楚,人们依照风格比较认为它与《卢切莱圣母》差不多属于同一时期或者更晚一点。作品有可能是佛罗伦萨圣三一教堂的修会委托的,瓦萨里说它一直在圣三一教堂的高坛上,直到1471年因为被另一位画家的作品取代而移到了教堂的一个侧坛。1810年,作品被移到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1910年进入乌菲齐。作品原先好像是一个方形板,后遭到切割,顶部两侧的两位天使被切除,形成了现在的尖顶板,框架也是1890年代修复的时候添加上去的。作品原貌的这些改变使得今天要对它进行完整的解释已经不可能。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正面对着观者的巨型宝座,宝座用科斯马蒂风格(Cosmatesque)的图案加以装饰,这个风格源自拜占庭,但中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在意大利流行,多用于装饰教堂地面、主教宝座和布道坛,“科斯马蒂”这个名称也是得自罗马的一个主做教堂装饰的家族,所以该风格已成为一种本地化的、带有某种传统记忆的符号。
宝座的下面有一个拱廊式的结构,三个半圆拱内安排了四位“旧约”先知的形象,两侧的两位先知都抬头看着宝座方向,中间两位先知则是正面的庄严造型。每个先知手上都展开了一页经卷,上面是对基督作为救主降临的预言。最左边是耶利米(Jeremiah),他的经卷上的文字来自《耶利米书》第31章第22节:“Creavit Dominus novum super terram foemina circundavit viro”(“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最右边是以赛亚(Isaiah),他的经卷上的文字取自《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Ecce virgo concipiet et pariet filium”(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中间半圆拱里的两个先知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王,他们代表耶稣的世系,亚伯拉罕的经卷文字取自《创世纪》第22章第18节:“In semine tuo benedicentur omnes gentes”(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大卫王的经卷文字取自《诗篇》第132章第11节:“De fructu ventris tui ponam super sedem tuam”(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四位先知虽然使用的是拜占庭式的金色基底,但中间凹形的半圆拱设计产生了十分独特的效果:它在横向上制造了一种背景—前景式的空间结构,仿佛四位先知就是坐在窗口一般;在纵向上,凹形拱顶与圣母宝座的基座和座位恰好同构,形成一种透视深度。
宝座上的圣母子和宝座两边八位天使的形象设计基本是拜占庭风格的延续。天使的头有节奏地向里或向外,形体的刻画比较有实体感。圣母子的刻画还是拜占庭风格,金线装饰再次出现在衣袍上。坦率地说,这件作品虽然在艺术家自己的创作历程中有一些局部改进,但从艺术史的意义上看,它并没有显示出太多令人侧目的地方。
四、乔托的综合
贝洛西在他的奇马布埃研究中评价说:
对意大利绘画的未来而言,13世纪80年代最具戏剧性,也最性命攸关。13世纪80年代初,奇马布埃是无可争议的明星,是每个人的参照点。到13世纪80年代末,事情发生了变化,锡耶纳画家杜乔·迪·博尼塞尼亚已经冉冉升起,在佛罗伦萨靠着《卢切莱圣母》的委托而声誉鹊起,这是13世纪最大的木板画,至少那时候的人是这么告诉我们的。进而,年轻的乔托的新观念——1286年他大约20岁——迎头赶上,靠着他的才华和非同寻常的人格,当然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奇马布埃还是最著名的画家,他事实上被邀请到阿西西装饰圣方济各大教堂,但他必须跟两个新生的天才竞争,后两位固然得益于他的教诲,但已经超越了他。14世纪初,他已经神秘地去到另一个世界,但丁在《神曲》中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诗文:“奇马布埃自以为在绘画方面擅长,如今乔托成名,使前者的盛名黯然失色。”[29]
的确,比起奇马布埃,乔托在艺术史中享有的盛名要坚实得多。他在阿西西圣方济各大教堂、帕多瓦阿雷纳礼拜堂,以及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巴尔迪礼拜堂绘制的壁画装饰堪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杰作;他为佛罗伦萨新圣母马利亚教堂绘制的巨型十字架是改造十字架图像形态的里程碑之一;他为罗马红衣主教绘制的双面祭坛画亦是该类型的早期经典;而他为佛罗伦萨万圣教堂(Chiesa di Ognissanti)高坛绘制的宝座圣母就像一篇结构严谨、语义宏赡的讲道文,他被置于意大利祭坛画早期历史的重要位置当之无愧。
万圣教堂是谦卑兄弟会(Humiliati)建造的,供奉的是所有圣徒和殉教者。谦卑兄弟会大约出现于12世纪,1201年得到教皇承认,然后在北意大利蓬勃发展,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势力达至顶峰,1298年对兄弟会组织的调查显示,它的机构达到389个,大部分在北意大利,其中托斯卡纳有5个,佛罗伦萨的万圣修道院则是托斯卡纳地区最大的组织机构。[30]1310至1320年,乔托在这里获得了一系列委托,宝座圣母是其中之一。
和奇马布埃在卢浮宫、杜乔在乌菲齐的宝座圣母一样,乔托也采用了方形板加尖顶的结构。但框架朴实无华,没有附加太多装饰。艺术家把全部的热情都放到了图像本身的“言述”功能上,即如何通过形象的组合和空间的配置来建立图像与祀拜的关联,让委托人的观念投射和仪式需求在图像中得到完满的体现。
实际上,作品在许多方面显示了艺术家对传统和创新的融合。比如金色基底、人物比例的等级划分属拜占庭传统,而宝座的装饰是杜乔在《卢切莱圣母》中使用过的哥特风格和奇马布埃在《圣三一宝座圣母》中使用过的科斯马蒂风格的结合,人物形象尤其圣母子形象的刻画则是在奇马布埃和杜乔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然主义再造。所以,艺术家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对多源头的吸收、融合和统一。
“Humiliati”这个名称表明,谦卑是兄弟会尊奉的最高美德。何谓“谦卑”?《马太福音》第23章第11—12节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第22章第25—26节也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意思是:谦卑就是要认识自己,认识到上帝才是生命的真理和道路。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根据福音书的教义和圣本笃的教导为谦卑列举了上升的十二个阶梯,升高的逻辑正好是世俗的社会秩序的倒置。伯尔纳的教诲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宗教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修会和兄弟会都是他的信奉者。乔托在图像中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阐释了谦卑的逻辑。
在中世纪的图像传统中,神圣形象的排列是遵循严格的等级秩序的,比如圣母宝座两侧,都是天使在上面,圣徒排在天使下面。可是,在乔托这里,我们看到,他在宝座下方安置了四位天使,天使上方是十位圣徒分列于宝座两侧。这一结构倒置就是对福音书和伯尔纳的谦卑概念的一种视觉传达,被置于上方的圣徒就是通过谦卑而获得精神提升,而天使在这里就代表谦卑美德的人格化形象,就是说它们在此不是作为天国等级的象征,而是作为通往天国的阶梯或道德保证被摆置在观者面前。宝座底下有两位站立的天使,手上分别拿着王冠和圣体盒模型,还有两位天使跪在地上,手上拿着百合和玫瑰,这些符号物象征了圣母的圣洁和基督的牺牲,圣母对上帝旨意——“道”以“肉身”的形式成就在她身上——的顺从和基督的上十字架,这本是就是对谦卑的践行,就是说,天使在此是作为美德的象征在场:“除了关心天使的自然本性,修会成员可能更关心将他们与天使联系起来的道德维度,这一维度是通过宣示守贫、慈善和顺从来强调的,因为这些行为可将他们和天国的圣徒、天使结合在一起。”[31]
同时,跪在地上的两位天使穿的不是那种彩色服装,就像我们在奇马布埃和杜乔那里看到的,而是兄弟会的灰白会衣。这表明,这两个天使的敬献还是对兄弟会祀拜仪式的操演,天使模仿跪在宝座前的供养人向圣母和圣子敬献象征牺牲和殉教的鲜花,上面还有两位天使,一位拿着王冠,一位拿着圣体盒,献给圣母子,进一步在视觉上强调了天使的敬献与献给圣徒和殉教者的万圣教堂的关联:“跪着的天使是僧侣做仪式的时候在圣坛前祀拜行为的再现。在他们与观者空间的邻近中,这些天使也发挥着中保形象的功能。通过向下模仿祀拜者的下跪姿态和向上对圣母子的凝视,天使还暗示了他们在宗教共同体当中的角色,比如向上帝报告他们的善举恶行。……因而,《万圣圣母》中的天使再现了天使参与宗教生活的重要性。他们体现了中保的精神力量和不同国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说是通过存在的精神秩序展示了向上和向下的运动。”[32]祭坛画对委托人的需求给以明确回应始于13世纪末,乔托在满足委托人诉求的时候充分调用了图像功能多层次、多向度的运作。
这件作品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关注:圣母子的表现。圣子如王者般坐在圣母腿上,眼睛凝视着左前方,右手做出祝福的手势,很显然,这里是把奇马布埃和杜乔的设计结合到了一起。圣母的形象描绘则更多体现了乔托自己的造型天赋,这是一个摆脱了圣像传统的圣母,是一幅人间母亲的肖像,她穿着灰白色上衣和蓝色斗篷,形体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刻画得极具体量感,尤其灰白色丝绸衬衣凸显的身体轮廓,赋予了圣母形象浓郁的现实气息。圣子祝福的手势放置在母亲胸口中间,似乎在刻意强调圣母作为教会之代理的“哺乳”或滋养生命的功能。周围的圣徒和天使的目光也都是汇聚于此,他们抬头看着圣母和圣子,借自杜乔的这个图像配置显然再次强化了圣母的谦卑美德。
奇马布埃、杜乔和乔托,三位艺术家在多源头相互作用的祭坛画语境中发展出各自的图像风格和语言表达方式,从而将意大利祭坛画从早期的拜占庭阶段推向了成熟。
[1] Hans Belting,Likeness and Presence: A History of the Image before the Era of Art, trans. Edmund Jephcot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ch. 4.
[2] Bissera V. Pentcheva,Icons and Power: The Mother of God in Byzanium(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University Park, 2006), ch. 3.
[3] 有关“十字军艺术”,最权威的研究参见Jaroslav Folda,The Art of the Crusaders in the Holy Land, 1098-1187(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Crusader Art in the Holy Land: From the Third Crusade to the Fall of Acre,1187-1291(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以及同一作者更为简明的综合研究参见Crusader Art: The Art of the Crusaders in the Holy Land, 1099-1291(Burlington: Lund Humphries, 2008).
[4] Jaroslav Folda,Byzantine Art and Italian Panel Painting: The Virgin and Child Hodegetria and the Art of Chrysograph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xxii.
[5] Folda,Byzantine Art and Italian Panel Painting, xxii.
[6] Ibid., 90.
[7] Kurt Weitzmann,The Icon: Holy Images - Sixth to Four-teenth Century(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8), 42.
[8] 有关这两件作品的技术分析和文献目录,参见:National Gallery of Art Online Editions,Italia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y Paintings(Washington: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2016), 136-147; 148-174. 亦可参见:Folda,Byzantine Art, 115-128.
[9] Raimond Van Marle,The Development of the Italian Schools of Painting1 (Berlin: Springer, 1923), ch. VI.
[10] 有关卢卡和比萨画派的早期历史,参见Victor Lasareff, “Two Newly-Discovered Pictures of the Lucca School,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51, no. 293 (Aug., 1927): 56-57; Victor Lasareff, “New Light on the Problem of the Pisan School,”Burlington Magazine68, no.395 (Feb., 1936): 61-73; Edward B.Garrison, “Toward a New History of Early Lucchese Painting,”The Art Bulletin33, no. 1 (Mar., 1951): 11-31.
[11] Lasaleff, “Problem of the Pisan School,” 61.
[12] Gertrude Coor-Achenbach, “A Visual Basis for 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Coppo di Marcovaldo and His Son Salerno,”The Art Bulletin28, no.4 (Dec., 1946): 234.
[13] James H. Stubblebine, “Byzantine Influence in Thirteenth-Century Italian Panel Painting, ” Dumbarton Oaks Papers 20 (1966): 93.有关这件作品其他方面更详细的讨论,参见Rebecca W. Corrie, “Coppo di Marcovaldo’s Madonna del Bordon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Bare-Legged Christ Child in Siena and the East, ” Gesta 35, no.1 (1996): 43-65.
[14] 具体的讨论参见Curt H. Weigelt, “Guido da Siena's Great Ancona: A Reconstruction,”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59, no. 340 (Jul., 1931): 15-17; 20-23; James H. Stubblebine, “An Altarpiece by Guido da Siena,”The Art Bulletin41, no.3 (Sep., 1959): 260-268; Victor M. Schmidt, “Thirteenth-Century Panel Paintings from Siena, Altenburg,”The Burlington Magazine143, no.1181 (Aug., 2001): 512-514. 对散落各地的饰板的考察,参见James H. Stubblebine, “An Altarpiece by Guido da Siena and his Narrative Style,”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58).
[15] Luciano Bellosi,Cimabue(New York, London, and Paris: Abbeville Publishing Group, 1998), 130.
[16] John White,Duccio: Tuscan Art and the Medieval Workshop(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9), 32-33.
[17] James H. Stubblebine,Duccio di Buoninsegna and his School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22.
[18] Luciano Bellosi, “The Function of the‘Rucellai Madonna’in the Church of Santa Maria Novell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61 (2002): 151-152.
[19] Francesco Albertini,Memorial of Many Statues and Paintings in the Illustrious City of Florence, ed. Waldemar H. de Boer & Michael W. Kwakkelstein, trans. Patricia Brigid Garvin and Waldemar H. de Boer (Firenze: Centro Di, 2010), 97.
[20] 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世纪的反叛》,刘耀春译,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2页。
[21] J. A. Crowe & G. B. Cavalcaselle,A New History of Painting in ItalyI (London: John Murray, 1864), 203.
[22] Josef Strzygowski,Cimabue und Rom: Funde und Forschungen zur Kunst-geschichte und zur Topographie der Stadt Rom(Wien: Alfred Hölder, 1888), 58.
[23] A. Venturi,Storia dell’Arte ItalianaV (Milano: Ulrico Hoepli, 1907).有关奇马布埃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Luciano Bellosi, “Introduction,”Cimabue.
[24] Hayden B.J. Maginnis, “Duccio’s Rucellai Madonna and the origins of Florentine painting,”Gazette des Beaux-Arts123 (Apr., 1994): 151.
[25] A. Venturi,Storia dell’ Arte ItalianaV, 78.
[26] Luciano Bellosi,Cimabue, 126-129.
[27] Holly Flora,Cimabue and Early Italian Devotional Painting(New York: The Frick Collection, 2006), 13. 作者说的最新研究是指2005年比萨举行的“奇马布埃与比萨”的展览上有专家提出的观点。
[28] James H. Stubblebine,Duccio di Buoninsegna and his SchoolI, 22.但贝洛西认为圣泽诺比乌斯的位置应当是圣哲罗姆,参见Luciano Bellosi, “The Function of the ‘Rucellai Madonna’ in the Church of Santa Maria Novella,”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61 (2002): 147-148.
[29] Bellosi,Cimabue, 126.
[30] Julia I. Miller and Laurie Taylor-Mitchell,From Giotto to Botticelli: The Artistic Patronage of the Humiliati in Florence(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5.
[31] Meredith J. Gill,Angels and the Order of Heaven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
[32] Miller and Taylor-Mitchell,From Giotto to Botticelli, 34.
原创艺术学研究 艺术学研究编辑部
吴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