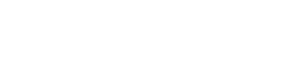内容提要:斯齐戈夫斯基1909年接替维克霍夫的教席,但在日后正统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学派历史建构中他基本上是被当做被放逐者,割席相待。学统上关联,学派上切割,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深层原因要在他们的艺术史方法的分歧之间去寻找。本文以1909年维也纳大学哲学院第二个艺术史教席的继任者选举风波和同年斯齐戈夫斯基的就职演说为切入点,浅析斯氏艺术史思想的主要框架内容及其与正统维也纳学派的冲突。
关键词:斯齐戈夫斯基 维也纳学派 艺术史方法 比较艺术学
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Josef Strzygowski)于1862年3月7日出生于今天波兰南部的加里西亚地区名为比亚拉(Biala)的小镇一个纺织厂主家庭。他早年先后于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修习古典考古学与艺术史〔1〕,1885年在慕尼黑大学以《耶稣的洗礼的图像志》(Ikonographie der Taufe Christi)一文通过博士答辩,1887年又在维也纳大学完成关于拜占庭艺术对于画家奇马布埃(Cimabue)影响的教授资格论文。1892年他成为格拉茨大学的首位艺术史教授,17年后于1909年被聘为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讲席教授,在那里任教至1933年退休,并于同一年在维也纳创立了比较艺术研究学会(Gesellschaft für vergleichende Kunstforschung),这一个学会的通报发行至今。1941年1月2日斯齐戈夫斯基逝世于维也纳。在他24年的维也纳大学任期中,斯齐戈夫斯基指导过的博士论文数量超过130篇,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同时任教的德沃夏克和施洛塞尔〔2〕。据贡布里希回忆,他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期间听过几次斯齐戈夫斯基的讲座,由于听众人数太多,使他没有兴趣继续听下去,在他眼中,“他是个领袖式的人物、富有魅力的演说家,许多人对之洗耳倾听,与施洛塞尔形成鲜明对比,人们要施加压力才迫使几个学生去后者那里,以免课堂彻底空荡荡。” 〔3〕
斯其戈夫斯基像
然而与当时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齐戈夫斯基在“二战”以后迅速被主流的艺术史界所遗忘,他的著作长期无人问津。作为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历史上的几位重要教授和比较艺术学的开创者,虽然在奥地利以及其他奥匈帝国原来的势力范围对他的关注和研究从未断绝,但在世界范围内对他关注的真正重新升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艺术史的发展,迟至20世纪最后十年〔4〕。斯齐戈夫斯基声誉在身前身后的巨大反差,两个重要的原因固然是他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学术思想的晦涩〔5〕,然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他与同时期维也纳学派尤其是与其主导人物施洛塞尔(Julius von Schlosser)的紧张关系和最终决裂。因此缘故,虽然斯齐戈夫斯基是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历史上一位无法回避的教授,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是被作为一个异端排除出维也纳学派历史的。这种紧张和对立关系其实在1909年斯齐戈夫斯基竞聘为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讲席教授的坎坷过程和他随后发表的入职演说中已经表露无遗。鉴于世界艺术史在国内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学界对于斯齐戈夫斯基这个关键人物了解尚少〔6〕,本文尝试从他在1909年选聘讲席教授的过程和他的就职演说作为切入点,分析他的艺术史方法的主要内容及其与维也纳学派治学方法的主要分歧。
这一段学术史上的公案,可以从施洛塞尔重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一篇重要论文讲起。在施洛塞尔于1934年发表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奥地利的德语学术研究百年回顾》(Die Wiener Schule der Kunstgeschichte: Rückblick auf ein Säkulum deutscher Gelehrtenarbeit in Österreich)长文中,他以自身为坐标点回溯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在维也纳的发展,正式将以维也纳大学为根据地的艺术史学派定名为维也纳学派,其核心人物依照执教的先后有艾特尔贝格尔(Rudolf Eitelberger,1847—1885)、陶辛(Moritz Thausing,1873—1883)、维克霍夫(Franz Wickhoff,1882—1909)、李格尔(Alois Riegl,1889—1905)、德沃夏克(Max Dvořák,1909—1921)、施洛塞尔(1892—1936),斯齐戈夫斯基赫然不在其列。扉页的赠献题词页显示,撰文的时机是奥地利历史研究所(Österreichisches Institut für Geschichtsforchung)成立80周年,题献的对象则为两人,分别是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冯·西克尔(Theodor von Sickel)和维也纳大学的艺术史家维克霍夫,题词上写的是纪念他们逝世25周年。
然而西克尔和维克霍夫并不在同一年去世,而是先后逝世于1908年和1909年。之所以于1934年同时纪念二人逝世25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撰文时二人去世皆未满26年,但更为可能的解释则是撰写此纪念文章具有明确的动机,意欲借助与血统纯正的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渊源关系以“判教”,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这一点在文章的开头第一段表述得更加明显:
“‘维也纳学派’这个表述所指为何,专业人士了然于胸:这是一个与奥地利的‘文书研究学院’——特奥多尔·冯·西克尔组建的历史研究所一直以来紧密相联的艺术史研究机构,其所在地是维也纳大学今日所谓的第二艺术史系,而这一称谓,顺便提一下,历史只有十年,它丝毫不表示年代先后,也根本不表示价值高下,这一点至多对于完全不了解学术惯例的人们可能是要说明的。特别是近来奥地利的诸多报纸反复报道,有可能造成完全错误的认识,因此之故,加之由于其他学术圈子对于这个长久以来享有盛誉、产生了如此多重要人物的‘学派’难以窥见全貌,下面会对其起源和发展略作勾勒。”〔7〕
从施洛塞尔的表述来看,当时大众媒体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第一艺术史系与维也纳学派一脉相承,而他所在的第二艺术史系则成立时间只有十年,地位上可能还略低。对此他要溯本清源,并与第一艺术史系划清界线。关于1909年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一分为二的历史,他随后在文中作了叙述。
“虽然当时任命的委员会(Kommission)以压倒性多数票(9票对2票)建议,以我为继任艺术史教席的第一(primo loco)候选人,德沃夏克为第二(secundo loco)候选人,保留条件是在完成接任维克霍夫的教席(Lehrkanzel)之后有可能会就进一步增加艺术史的课程提出申请,而少数派则提议,以自1892年起在格拉茨任艺术史正教授的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为维克霍夫的唯一(unico loco)继任者,附以相反的保留条件,即课程的进一步扩大须根据奥地利历史研究所(作为‘维也纳学派’所在地)的需要采取措施。在1909年7月3日召开的学院大会(Fakultätssitzung)上发生了罕见的事情,多数派的提议被否决,但反方仅占微弱多数,而且经过了十分激烈而漫长的辩论……故而在1909年7月7日继续进行的大会采纳了一个折中方案,据此建议除斯齐戈夫斯基外又以德沃夏克为艺术史正教授。这个提议(再次经过长时间辩论)得以通过并被政府批准。从此,存在两个教席和两个艺术史系(自我入职以来才经我建议称为第一和第二艺术史系)。‘第二艺术史系’就其历史而言乃是‘第一艺术史系’,且在人员兼职上也与常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旧日大本营的历史研究所相联,实际上不间断地延续了它的传统;而另一个为斯齐戈夫斯基新建的艺术史系,符合其特殊的宗旨和目的,而它们与维也纳学派的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常常是故意背道而驰,因此在勾勒我们的历史时只能对之完全不予考虑。”〔8〕
在施洛塞尔的叙述中,维也纳大学艺术史教席于1909年开始由一个变为两个,也是于这一年由一个艺术史系裂变为两个艺术史系,他开始执掌其中一个教席(1921年)后,建议称斯齐戈夫斯基所在的艺术史系为第一艺术史系,而他所在的则称为第二艺术史系。然而根据笔者所在的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主页的介绍,维也纳大学的第二个教席(Lehrstuhl)出现得更早:“不过特别的是,早在19世纪,从1879年开始就设立了第二个艺术史教席,掌此教席者先是陶辛(1838—1884),自1885年起是维克霍夫(1853—1909),自1909年是斯齐戈夫斯基(1862—1941)。艾特尔贝格尔的教席则直到1897年才由李格尔(1858—1905)填补,随后德沃夏克(1874—1921)于1909年,施洛塞尔(1866—1938)于1922年,泽德尔迈尔(1896—1984)于1936年相继继任。”〔9〕
照此当代的官方表述,斯齐戈夫斯基的教席实则传承有绪,其前任正是维克霍夫,而1909年看似新设立的教席其实也是援引先例,1897年至1905年间维也纳大学实际上有两位艺术史正教授:维克霍夫和李格尔,只是李格尔英年早逝,其教席在随后的四年里无人填补而已。如此看来,施洛塞尔在重构维也纳学派时将维克霍夫这一支纳入师承谱系,而单独将斯齐戈夫斯基剔除,实则更多是出于二者学术观念上的格格不入而做出的举动。〔10〕
关于1909年的这场选举风波,从当时的会议记录来看,有着不同于施洛塞尔的更为详细的记述。1909年6月,维克霍夫逝世后两个月,挑选其继任者的委员会第一次开会,当时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冯·奥滕塔尔(Emil von Ottenthal)要求选举施洛塞尔,而持相反意见的反方发言人为化学家韦格沙伊德尔(Rudolf Wegscheider),他显然是有备而来,为支持他推荐的斯齐戈夫斯基而引述了一系列鉴定意见,其撰写者包括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德希奥(Georg Dehio),赖那克(Salomon Reinach),冯·贝尔歇姆(Max von Berchem),戈尔德施密特(Adolph Goldschmidt),冯·比辛(Friedrich Wilhelm von Bissing)。此外韦格沙伊德尔论辩道,最终有两个教授席位要被占据,而德沃夏克还只是编外教授(Extraordinarius)。当时的会议上历史学家们的意见胜出,他们提议选举施洛塞尔和德沃夏克,而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韦格沙伊德尔则赢得了印度学者冯·施罗德(Leopold von Schröder)的支持,提交了招募斯齐戈夫斯基的议案。他虽然失败了,但是依然宣布了少数派表决意见(Minoritätsvotum),其中他指出斯齐戈夫斯基是“奥地利在世的艺术史家中最优秀者”,“他不轻视历史—语言学的细节,但也不沉溺于此”,最关键的是他强调,“维也纳大学艺术史教席的填补不能够也不应该由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特殊利益的相对狭隘的观点加以决断(die Besetzungder kunstgeschichtlichen Professur an der Wiener Universität nicht von dem relativ engen Gesichtspunkte der speziellen Interess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beurteilt werden kann und darf)”,而历史研究所的利益依然将由德沃夏克的工作得到保障〔11〕。7月3日在院内就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少数派表决意见举行了辩论。讨论激烈,持续到夜间23点,最后由韦格沙伊德尔和冯·施罗德撰写的少数派表决意见确定无疑胜出,斯齐戈夫斯基明显赢得了选举。四天后学院代表又坐到一起开会,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一方面招募斯齐戈夫斯基作为维克霍夫的继任者,另一方面拟定德沃夏克作为李格尔原来教席的讲席教授。二人皆于1909年10月1日履新上任。
由此可见,1909年在维克霍夫教席继任者的竞选之中,对于这个教席与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关系的权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化学家韦格沙伊德尔所提交的少数派表决意见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他的提案中已经有一个教席顾及了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利益,则另一个教席也就是维克霍夫教席不能完全偏向奥地利历史研究所。显然这一点最终打动了哲学院的多数与会者,使得少数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当时的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并不下属哲学院,甚至独立于维也纳大学〔12〕,然而由于维也纳大学第一位艺术史教授艾特尔贝格尔与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密切关系和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之后多位艺术史教授都出自该所。这种倾向性在他于1873年选择陶辛为维也纳大学的第二个艺术史教授的推荐评语中已然明显,他说自己之所以看重陶辛,是“因为他出身历史学,因而有可能使文化历史因素的优势得到恰当的发挥(weil dieser von historischen Studien ausgegangen sei, und damit das kulturhistorische Moment gehörig zur Geltung bringen könne)”〔13〕。那一年陶辛是奥地利历史研究所成员,他在开始艺术史研究之前专长是中世纪历史和历史史源学。1880年陶辛成为讲席教授,四年后逝世,他的教席由同样是艾特尔贝格尔推荐的维克霍夫继任(一开始是作为编外教授),而维克霍夫也是出自奥地利历史研究所,而“那里所坚持的方法看来正是他分析艺术问题的真正基础”。维克霍夫当时仅有28岁,他的获选在哲学院并非没有异议,在学院成员看来这代表着奥地利历史学院的诉求〔14〕。1885年艾特尔贝格尔逝世,一年后在其继任者的职位要求中哲学院与奥地利历史学院的矛盾已然表面化:“艾特尔贝格尔所规定的工作方式和在设立第二个艺术史教席之际任命维克霍夫时已经作为基础的考虑,是强烈的历史学背景和与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具体关联,二者最近已被作为行动的基础,由此对于艾特尔贝格尔的继任者席位提出了这样的职责要求,所要找到的专业人员应当能够同时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代表这个学科,既更多考虑学科的整体,也就是说理所当然要更多考虑艺术研究的美学因素,也更少强调奥地利的境况(这在事实上通过第二个教席的强有力的史源学导向的研究和就其为国家所设定的目标而言已然给定)。〔15〕”这样的人选迟迟而不可得,直到1894年李格尔才在学院大会上被一致挑选为候选人,1897年他升任讲席教授。
虽然李格尔与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关系密切,然而从1886年的这个职位描述中可以读出明显的冲突意味。对于艾特尔贝格尔而言,他特别看重的是继任者的历史学背景和史源学研究,尤其是偏向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引以自豪的严格的史料考订,然而对于哲学院的其他同事而言,他们不希望两个艺术史教席都成为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附庸”,故而在职位描述中特别提出了更多考虑“艺术研究的美学因素(ästhetischen Moments der Kunstbetrachtung)”的要求。维也纳大学哲学院与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在利益诉求上的冲突在1909年维克霍夫教席继任者的竞聘中再次爆发。少数派的代表虽是一个化学家,但他最终以两个教席的设置和人选要求不能都偏向奥地利历史研究所为由说服了学院的大多数成员,从而选择了斯齐戈夫斯基。
斯齐戈夫斯基曾经在维也纳大学求学,当时的艺术史教席正是艾特尔贝格尔,学统上他与狭义的维也纳学派其实存在着渊源。所以在他被选为讲席教授的一个月后于1909年11月3日所作的入职演说《维也纳大学的艺术史》(Die Kunstgeschichte an der Wiener Universität)中,在开头便回忆起1882—1883学年他作为学生坐在艾特尔贝格尔的“病榻”旁,这位长者的“人格”给他留下了难以释怀的印象。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个演说中,他第一次比较清晰完整地阐述了自己想要开拓的艺术史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并由此展示了与正统维也纳学派在学术思想上的分歧,为日后二者的决裂埋下了种子。
斯齐戈夫斯基随后指出,艺术史的讲席教授只能出自奥地利历史研究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艺术史在维也纳的奠基教授是艾特尔贝格尔,他的授课范围原先涵盖了整个艺术史,包括古代,故而他斯齐戈夫斯基并不愿接受在他看来随意的学科界限划分:考古学家康策(Alexander Conze)讲授古代艺术史而陶辛讲授之后时代的艺术史。他认为艺术史应当拥有更广阔的舞台,因为图像分析的问题对于诸多其他领域也已经具有了未曾料想到的意义,例如亚述学、埃及学。在此涉及的不仅是图像志的分析,而且首先是解读在“艺术形式本身之中蕴藏的价值”。对于他来说,图像研究将成为跨学科的要求,“因为这样的一种认识已经到处觉醒,即艺术品也说一种科学语言,而且使之如同文字语言一般对于各种科学也同样可以解读的时机已然成熟(weil allgemein die Erkenntnis erwacht ist, dass auch das Kunstwerk eine wissenschaftliche Sprache redet und es an der Zeit wäre, sie für die einzelnen Wissenschaften ebenso lesbar zu machen, wie die Schriftsprache)。”他随后还展望了他心目中艺术史的学科定位和涵盖范围:“艺术史是普通艺术学的一部分,它尤其包含了造型艺术领域,其中包括建筑艺术、手工艺、装饰、雕塑、素描、绘画和一些中间领域如园林、书籍艺术等,总之包括由人手所塑造的,意在给眼睛传达艺术印象的一切。” 〔16〕为此他更细细列出了艺术史所要处理的六个不同的范畴。
1. 地点范畴,指文物的编目和保护。
2. 时间范畴,指处理个别物品的所有历史手段,尤其指相关文字资料的史源学。在这个范畴中斯齐戈夫斯基特别针对的是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其结果是艺术家传记和艺术家辞典。
3. 造型艺术的本质(Wesen der bildenden Kunst),这个范畴斯齐戈夫斯基认为是艺术品特有的,分析的总是具体的艺术品,包括其技法(Technik)、材质(Material)、题材(Gegenstand)、形状(Gestalt)。他所理解的题材是艺术品的主题,但对之的把握除了需要单纯的知识以外也要求一种“移情”,而形状显示了艺术品与自然界中原型的直接关联。题材和形状由此构成了艺术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在此之上艺术得以表达:“题材和形状自身是非艺术的前提,艺术家以之为容器,在其中倾注他想要表达的东西(Gegenstand und Gestalt sind die an sich unkünstler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en sich der Künstler bedient, um in sie als Gefäß das zu gießen, was er zu sagen hat)”。反之,艺术的价值作为艺术品的核心则毋宁是隐藏于“内容与形式(Inhalt und Form)”之中。形式可视为自然惯例的具体化,使得各种形状如“光线、空气和色彩根据深度造成想要的效果(Licht, Luft und Farbe der Tiefe nach zur beabsichtigten Wirkung)”。对他而言艺术品的“内容”则是其中“挣扎着想要得到表达的精神力量,由此力量题材和形状得以被选择并赋予一定的形式(nach Ausdruck ringende seelische Kraft, aus der heraus der Gegenstand und die Gestalten gewählt und in eine bestimmte Form gebracht)”。故而斯齐戈夫斯基所理解的艺术品的“内容”与事实的再现无关,而是指艺术家在使一件作品变为实物之前的状态,指创作者的精神和心理状况。这种艺术的塑造的物质和观念/精神之间的关联及其相互制约正是斯齐戈夫斯基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种艺术品的形式与艺术家心境之间的依存性日后被他推广至整个民族、国家与其艺术的层面。由此斯齐戈夫斯基提出了“比较艺术史”(vergleichende Kunstgeschichte),在这样的艺术史中强调“质的事实作为组织全部材料的基础(qualitativen Tatsachen zur Grundlage der gesamten Anordnung des Stoffes)”。这里提到的“质的事实”正意味着对传统艺术史分类模式的重新评价。斯齐戈夫斯基的目标不再是将一件人造物置于尽可能准确的历史序列之中,而是根据对“艺术品质”(künstlerischen Qualitäten)的分析“组织全部材料”。
4. 艺术价值的变迁与特定文化史背景之间的关联,这个关联首先是“自然条件,(文化)孩童时期依据种族、民族、土地和气候的发端,然后由个性的概念及其与文化与世界观的关系出发,风格的形成与过渡时期”,斯齐戈夫斯基称这样的概观为“综合的(synthetische)”。这样的研究会导向以“文化圈”(Kulturkreise)为结构的艺术发展史的知识。
5. 艺术品的观者,但研究不采取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而是以“品鉴”(Geschmacksurteil)和“批评”的历史为中心。
6. 艺术史的教学和研究,包括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教学和学科史。〔17〕
斯齐戈夫斯基作这个演讲时47岁,他的思想已成形,演讲勾勒了他的艺术史思想梗概,可以看做是他后期著作的纲领。在六个范畴中第三个是最复杂的,他于1912年的论文《艺术研究的系统和方法》(System und Methode der Kunstbetrachtung)以表格说明这个范畴提到的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他的学生,后来流亡至美国的东亚艺术史学者萨尔摩尼(Alfred Salmony)又将表格译作英文〔18〕。很显然在这个作为斯齐戈夫斯基核心思想的范畴中并无传统的维也纳学派的一席之地,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引以为傲的史源学研究被归入了第二范畴,一个并不太重要的位置,而且被认为是艺术史的辅助性研究,而不针对艺术史的核心问题。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最核心的是“观看(Anschauung)”,因为它可以逼入“造型艺术的本质”,由此推导出“图像语言的语法”,而相形之下,语言学—历史学或者传记式的研究方法则可加以忽略。这样的观点和对比对于那些情感上归属于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听众而言,不啻挑衅。
显然1909年的演讲没有弥合新入职的斯齐戈夫斯基与正统维也纳学派之间的分歧,反而将之扩大。在他入职后两年即1911年,维也纳大学的两个艺术史教席之间作了空间上的分隔,哲学院为斯齐戈夫斯基单独租了一个房间。从此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的教学队伍实际上一分为二,两个教席之下学生们的选课各自独立。一开始,德沃夏克执掌教席期间,学生论文的答辩还各自在对方的教学空间举行。等到1921年施洛塞尔就职,双方的矛盾激化至水火不容,遂各自成立艺术史系,维也纳艺术史系彻底分裂,斯齐戈夫斯基正式被清除出正统维也纳学派阵营,他的教席在他于1933年退休后也没有再继续委任新人,而是被废置。1936年泽德尔迈尔继任施洛塞尔的教席,在他手中分裂的维也纳艺术史系复归统一。在施洛塞尔以及他之后对于维也纳学派历史的重构中,斯齐戈夫斯基被放逐,逐渐被人遗忘。然而他因在传统艺术史领域之外的奋力开拓,使其成为世界艺术史的拓荒者,并给今日的维也纳艺术史系留下了宝贵的隐形遗产。2012年,维也纳大学增设伊斯兰艺术史教席,2016年新增东亚艺术史教席。
究实而论,斯齐戈夫斯基与正统维也纳学派在艺术史方法上的纷争,并不简单是比较分析—形式分析或者精神史研究—史源学研究之争。诚如埃尔斯纳所言,维也纳学派中的李格尔的艺术史思想同样晦涩而充满争议,同样与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相互纠缠。“在维也纳的文化语境中,这在当时是一种尝试,想要书写一部客观的艺术史,但其中却包含着主体性问题——这一科学的任务与当时在同一城市中的胡塞尔和弗洛伊德的工作相平行。”李格尔和斯齐戈夫斯基关心的都是艺术本身的文化意义问题,他们的工作都根植于一个结构精巧的哲学命题,或者受其引导〔19〕。所不同的是,李格尔后来成为艺术史英雄,而斯齐戈夫斯基则被放逐至沉默的荒蛮之地。二者身后境遇的巨大差异,或许也是今日斯齐戈夫斯基重新引发学界对其艺术史思想关注的背景之一。
注释:
〔1〕本文中将Kunstgeschichte译作艺术史,而不译作美术史,原因在于Kunst这个词泛指艺术,德语中如果表示具体的艺术,则在它之上加以限定词,如bildende Kunst(通常作复数Künste),而中文中在翻译bildende Kunst时一般译作“造型艺术”,并不译作“造型美术”。鉴于在一个文本翻译中意义相同的同一个外语词尽量译作同一个词的原则,本文采纳“艺术史”的译名。
〔2〕齐坎(Josef Zykan)《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七十寿诞学生纪念文集书评》(Reviewed Work: Zum 70. Geburtstag dargebracht von seinen Schülern by Josef Strzygowski-Festschrift),载于《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1935年,第5卷第1期,第90页。
〔3〕“Er war ein Demagoge, ein hinreißender Redner, dem eine große Menge lauschte, im Gegensatz zu Schlosser, wo man ein paar Studenten fast zwingen mußte hinzugehen, damit die Bänke nicht ganz leer waren.”参见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倘若你们当真要说些什么:艺术研究中的转变》(Wenn’s euch Ernst ist, was zu sagen: Wandlungen in der Kunstbetrachtung注:这里贡布里希玩了一个语言游戏,他的名Ernst在德语中也有严肃、较真的意思),载于西特(Martina Sitt)编《艺术史家自述:十个自传速写》(Kunsthistoriker in eigener Sache: 10 autobiographische Skizzen),柏林:Reimer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4〕斯齐戈夫斯基是第一代明确将研究领域拓展出欧洲之外的艺术史家,不过虽然他声称要研究整个世界的艺术,但他的研究范围主要还是聚焦于欧亚大陆,而甚少涉及南美洲、非洲、大洋洲。他于1901年出版的《东方或罗马:古典时代晚期和早期基督教艺术史论文集》(Orient oder Rom: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spätantiken und frühchristlichen Kunst),不仅与李格尔一样对于古典时代晚期(Spätantike)成为重要的研究时段有开创之功,而且提出了东西方文化早期是否相互影响的大问题,例如他认为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整体上与同时期的中国艺术平行发展,并未对中国艺术施加明显的影响,相反中国艺术对于罗马艺术有所影响。除了在学术研究中他不自限于欧洲老窝,而且他在学术机构的设立上也有长远的计划,1912年他曾经尝试在德黑兰和北京设立两个分支研究机构,最终无奈因为经费问题而作罢。1918年斯齐戈夫斯基出版的《亚美尼亚和欧洲的建筑艺术》(Die Baukunst der Armenier und Europa)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亚美尼亚的建筑古迹的专著,对于东欧和南欧除意大利之外国家艺术的研究也有开拓之功。斯齐戈夫斯基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主要以德文论述,国内对其著作的译介几乎为空白。约翰斯(Karl Johns)在2017年初步整理了他的著述目录,长达47页,参见Karl Johns《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Josef Strzygowski,1862—1941),载于《艺术史学期刊》(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2017年,第17期,第1—47页。其中1923年的《精神科学的危机:以造型艺术研究为例,一次基础性框架研究尝试》(Die Krisis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vorgeführt am Beispiele der Forschung über bildende Kunst; ein grundsätzlicher Rahmenversuch,维也纳:Schroll出版社,1923年)可以看作是他关于世界艺术史方法论的一个较为详尽的论述。在他晚期的著作中以1930年的《亚洲造型艺术管窥,其本质与发展:一个尝试性研究》(Asiens bildende Kunst in Stichproben, ihr Wesen und ihre Entwicklung: ein Versuch,奥格斯堡:Dr. B. Filser出版社,1930年)为重要。
〔5〕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称斯齐戈夫斯基为“艺术史的阿提拉”,参见Bernard Berenson《造型艺术中的审美和历史》(Aesthetik und Geschichte in der Bildenden Kunst),苏黎世:Atlantis出版社1950年版,第21页。斯齐戈夫斯基的学生察洛斯科(Hilde Zaloscer)证实他确实亲近纳粹,参见Hilde Zaloscer《艺术史与纳粹主义》(Kunstgeschicht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载于施塔德勒(Friedrich Stadler)编《连续与断裂:1938-1945-1955》(Kontinuität und Bruch 1938-1945-1955),维也纳、慕尼黑:Jugend & Volk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6〕知网上迄今尚无对于斯齐戈夫斯基的专门研究,在少数相关论文中以下面三篇涉及较多:普菲斯特雷尔(Ulrich Pfisterer)的《世界艺术史的起源和原则》(李修建译,载于《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第155—163页),提到了他的两本著作《东方或罗马》(Orient oder Rom,德文原文误作Orient und Rom)和《精神科学的危机》(Krisis der Geisteswissenschaft,德文引文原文如此)。吴瑞林在其硕士论文《“东方来源”问题之学术史研究》(中央美院,2016年,尤其见第18-28页)对于斯氏的亚美尼亚建筑研究作了简要介绍。关于维也纳学派的分裂,戴丹在《从实证主义到形式分析——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形成》一文中(《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7 期,第1–8页)指出“当时大学里错综复杂的政策以及奥地利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Archduke Franz Ferdinand,1863—1914)力荐来自奥地利格拉茨的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后者成为了艺术史学院院长”。然而对于这一说法没有给出具体的出处。类似的论述见于网上数据库《艺术史家词典》(Dictionary of Art Historians)斯齐戈夫斯基词条(https://arthistorians.info/strzygowski),其中引用的Marchand(Suzanne L. Marchand)的论文《人工制品的修辞和古典人文主义的衰落:以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为例》(The Rhetoric of Artifacts and the Decline of Classical Humanism: The Case of Josef Strzygowski),刊于《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1994年,第33卷第4期,第120页)对于选举过程有稍为详尽的记述。文中提到费迪南大公可能在选举中给了斯齐戈夫斯基一臂之力,但这只是作者的一种猜测,其给出的理由是大公不喜欢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而倾向于德意志民间艺术,因而他可能成为斯齐戈夫斯基理想的赞助人。文章为此引用了霍勒( Gerd Holler)所著《奥地利-埃斯特的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 von österreich-Este,维也纳:Ueberreuter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一书中斯齐戈夫斯基的话,斯氏曾经在私人印行的《维也纳大学艺术史讲席和与之相联的第一艺术史系》(Das Ordinariatfür Kunstgeschichte und das damit verbundene I. Kunsthistorische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Wien,刊行于奥地利霍恩,1933年,第3页)提到,斐迪南大公正式批准了他的任命。然而仅从斯氏的这一极简的非公开言论,并不足以推断出他成功受聘于维也纳大学的主导因素是斐迪南大公的助力。下文将分析选举过程的一波三折和各派势力的较量。
〔7〕“Fachleute wissen sofort, was mit dem Ausdruck, Wiener Schule” gemeint ist: die mit derösterreichischen, école des chartes‘, dem von Th. von Sickel organisierten Institut für Geschichtsforschung von altersher engverbundene kunsthistorische Lehrstätte, die heute in dem sogenannten II. Kunsthistorischen Institute der Universität Wien ihren Sitz hat-eine Bezeich-nung übrigens, die erst ein Dezennium alt ist und in keiner Weise eine chronologische oder gar qualitative Wertung ausdrü-cken soll, was man höchstens denen sagen müßte, die mit akademischen Gepflogenheiten gänzlich unvertraut sind. Nament-lich in jüngster Zeit haben die österreichischen Tageszeitungen wiederholt Mitteilungen gebracht, die zu einem völligen Ver-kennen der Sachlage führen können: deshalb, und weil auch weitere wissenschaftliche Kreise über die Geschichte dieser längst in hohem Ansehen stehenden, Schule”, die so viele bedeutende Männer hervorgebracht hat, schwerlich ganz im Bilde sind, soll im folgenden eine rasche Skizze ihres Ursprungs und ihrer Entwicklung gegeben werden.”原文引自施洛塞尔(Julius von Schlosser)《维也纳艺术史学派》(Die Wiener Schule der Kunstgeschichte,因斯布鲁克:Wagner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第10页。另一个版本的中文译文参见施洛塞尔著,陈平编选《维也纳美术史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8〕原文见施洛塞尔《维也纳艺术史学派》(Die Wiener Schule der Kunstgeschichte),1934年,第50—51页。另一个版本的中文译文参见陈平编选《维也纳美术史学派》,2013年,第13页。
〔9〕“Einzigartig ist jedenfalls, dass bereits im 19. Jahrhundert, ab 1879, ein zweiter Lehrstuhl für Kunstgeschichte eingerichtet wurde, auf dem zunächst Moritz Thausing (1838-1884), ab 1885 Franz Wickhoff (1853-1909) und seit 1909 Joseph Strzy-gowski (1862-1941) wirkten. Eitelbergers Lehrstuhl wurde erst 1897 mit Alois Riegl (1858-1905) wiederbesetzt, dem 1909 Max Dvořák (1874-1921),1922 Julius von Schlosser (1866-1938) und 1936 Hans Sedlmayr (1896-1984) folgten.”这段简介的撰写者为哈特穆特(Maximilian Hartmuth)、毛雷尔(Golo Maurer)和罗森伯格(Raphael Rosenberg),参见https://kunstgeschichte.univie.ac.at/ueber-uns/geschichte-des-instituts/。舍得尔(Schödl)指出第二个教席(Lehrkanzel)设立于1873年。参见Heinz Schödl《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论其思想的发展》(Josef Strzygowski-zur Entwicklung seines Denkens),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Vienna,2011年,第29页。不过当1873年这个教席为陶辛所占据时他还只是个无讲席的编外教授,直至1879年他才升任讲席教授(Ordinarius)。
〔10〕关于施洛塞尔和斯齐戈夫斯基之间深刻的矛盾及其解读,参见弗罗德尔-克拉夫特(Eva Frodl-Kraft),《一个困境及其阐释的尝试: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对尤利乌斯·冯·施洛塞尔》(Eine Aporie und der Versuch ihrer Deutung. Josef Strzygowski – Julius v. Schlosser),载于《维也纳艺术史年鉴》(Wiener Jahrbuch für Kunstgeschichte),1989年,第42卷第1期,第7—52页。
〔11〕参见舍得尔《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论其思想的发展》,第32—33页。原始记录见《因枢密顾问维克霍夫逝世而为艺术史教席的重新委任所设的委员会的报告》(Bericht der Kommission zur Wieder-besetzung der durch den Tod Hofr. Wickhoffs erledigten Lehrkanzel für Kunstgeschichte),1909年7月3日,大学档案(Universitätsarchiv),哲学学院记录,斯齐戈夫斯基文件夹。
〔12〕1909年时维也纳大学下设四个学院,包括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后来学院数量逐渐增加,今日在医学院已经独立为维也纳医学大学的情况下,各学院和中心的数量依然达到了18个。目前艺术史系不再属于哲学院,而隶属于历史文化学院(Historisch-Kultur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历史上长期是独立的研究所,直到2016年才并入维也纳大学,隶属于历史文化学院。
〔13〕霍夫莱希纳(Walter Höflechner)、布鲁格(Christian Brugger)《维也纳、布拉格、因斯布鲁克大学艺术史的建立及其至1938年历史的概览》(Zur Etablierung der Kunstgeschichte an den Universitäten in Wien,Prag und Innsbruck. Samt einem Ausblick auf ihre Geschichte bis 1938),载于霍夫莱希纳(Walter Höflechner)、波哈特(Götz Pochat)编《格拉茨大学艺术史百年:附奥地利德语大学至1938年该学科历史概览》(100 Jahre Kunstgeschichte an der Universität Graz: mit einem Ausblick auf die Geschichte des Faches an den deutschsprachigen österreichischen Universitäten bis in das Jahr 1938),格拉茨:Akademische Druck-und Verlagsanstalt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4〕霍夫莱希纳《维也纳、布拉格、因斯布鲁克大学艺术史的建立及其至1938年历史的概览》,第26页。
〔15〕“Durch die von Eitelberger vorgegebene Arbeitsweise und durch den Umstand, dass mit der Ernennung Wickhoffs die seinerzeit schon anlässlich der Installierung der zweiten kunsthistorischen Lehrkanzel zugrundegelegten Überlegungen–die starke historische Bindung und die konkrete Einbindung in das Institut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neuerlich zur Grundlage des Handelns gemacht worden waren, ergab sich für die Nachfolge Eitelberger die Verpflichtung, einen Fachmann zu finden, der gleichsam in übergeordneter Position, unter stärk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Gesamten des Faches, und das hieß unausgesprochenermaßen auch unter stärk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ästhetischen Moments der Kunstbetrach-tung, und auch mit geringerer Akzentuierung auf die österreichischen Verhältnisse (welche durch die stark quellenorientierte historische Forschung auf der zweiten Lehrkanzel aus der Sache heraus und auch im Sinne der für den Staat verfolgten Ziel-setzungen gegeben war) das Fach zu vertreten in der Lage sein sollte.”参见霍夫莱希纳《维也纳、布拉格、因斯布鲁克大学艺术史的建立及其至1938年历史的概览》。也参见舍得尔《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论其思想的发展》,第30页。
〔16〕斯齐戈夫斯基(Josef Strzygowski)《维也纳大学的艺术史》(Die Kunstgeschichte an der Wiener Universität),载于《奥地利瞭望:德意志文化与政治》(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 Deutsche Kultur und Politik),1909年第21卷第5期,第396页。
〔17〕斯齐戈夫斯基《维也纳大学的艺术史》,第399页。转引自舍得尔《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论其思想的发展》,第37—40页。
〔18〕关于萨尔摩尼在斯齐戈夫斯基门下学习以及他日后在德国和美国研究东亚艺术史的情况,参见奥雷尔(JuliaOrell)《维也纳的早期东亚艺术史及其发展轨迹:约瑟夫·斯齐戈夫斯基、卡尔·维特、阿尔弗雷德·萨尔摩尼》(Early East Asian Art History in Vienna and Its Trajectories: Josef Strzygowski, Karl With, Alfred Salmony),载于《艺术史学期刊》(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2015年,第13期,第1—32页。关于世界艺术史在德语国家大学的发展概况,参见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艺术史与世界艺术史》(Kunstgeschichte und Weltkunstgeschichte),载于《世纪》(Saeculum),1989年,第40卷第2期,第136—141页。
〔19〕埃尔斯纳(Jaś Elsner)《古典时代晚期的诞生:李格尔和斯齐戈夫斯基在1901年》(The Birth of Late Antiquity: Riegl and Strzygowski in 1901),载于《艺术史》2002年第25卷第3期,第359—360页
陈亮 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