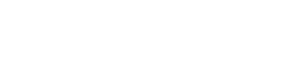内容摘要:晚清遗民在民国史中是被创新话语遗忘的群体。但在中国文化心理由古典型进入现代型的转折期,他们面对新时代的“旧知识”,折射出传统儒学遭遇的全新挑战。本文以有清宗室画家溥心畬的“归城”事件为起点,考证、梳理了晚清遗民群体的心理变迁。围绕出世、入世之经典话语模型,本文着力探析了这一特殊群体践行“家国天下”之文化策略的现实际遇。
关键词:晚清遗民 出世 入世 精神分析
一
后世文献中,溥心畬从戒台寺搬回恭王府,被描述为偶然机缘所致——贺姑母之寿。始作俑者,自然是这位署名“旧王孙”的恭亲王奕䜣之孙。1953年夏,他在陈隽甫买的一本《西山集》(卷一)后题云:“余自十八岁隐居马鞍山戒台寺,奉母读书之暇,喜习吟咏,年二十九为先姑母荣寿固伦公主寿,始出山。居城中,取所作诗印百册,后尽散去,且少作亦不留稿矣。此册为陈隽甫买于书肆者,诗虽无可存,而陈生之意亦可感矣。癸巳夏五月,二十八年后重题,心畬。”〔1〕“因姑母寿始出山”之说,在流传广泛的《溥心畬学历自述》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因荣寿公主七十正寿(荣寿公主系余姑母),遂奉先母移城内居住。”〔2〕
荣寿公主(1854—1924)为奕䜣长女,生于农历二月二日。清咸丰十一年封固伦公主,恭亲王固辞,改荣寿公主。光绪间,晋封荣寿固伦公主。12岁嫁富察志端,17岁守寡,与慈禧为伴。辛亥后深居简出,遗民圈尊其为“长公主”。如此一位显赫姑母的寿辰,对溥心畬而言自然重要,出山贺寿也是必然。但这与回城定居有怎样的因果关系?溥氏语焉不详。然,此等琐事既为当事人澄清,后世没有不信的理由。现行王家诚的《溥心畬年谱》、詹前裕的《溥心畬生平大事年表》、林铨居的《溥心畬年表》、王彬的《溥心畬简明年表》、龚敏的《溥心畬年谱》及台北故宫《溥心畬先生诗文集》所附年谱等,皆用此说。众家之言,口径一致,与溥氏本人“达成共识”。于是,关乎“返城”几乎无需再辩。事实果真如此?荣寿公主七十正寿为该年二月二日(1924年3月6日),若定居城内因为贺寿,那此后则应居于城内。但《西山集》(卷三)与《寒玉堂集》(卷上)分别收录《秋日将出山感怀》《甲子秋日将出山感怀》,虽诗名有别,实为一首:“天风吹河汉,列星西南驰。香飘月中桂,空阶露华滋。岭上白云不相待,秋光欲尽归莫迟。”〔3〕其中,“归莫迟”尽显溥氏“返城”之切。何事催人?显然非姑母之寿。“甲子秋日”距荣寿公主“正寿”已过数月。若因祝寿移居城内,何以“秋光欲尽归莫迟”?
“甲子秋日将出山”与多年后溥氏自述的“出山动机”,时间上有所出入。大量诗文显现他在姑母“七十正寿”后仍居西山,并未“奉先母移城内居住”。《西山集》(卷三),甲子夏秋之际诗篇达二十多首。从《甲子夏六月山雨连夕岩壑出云坐涧桥观瀑清风时来山翠流滴即景赋此》到《秋日将出山感怀》,中有:《西山石多橡树作橡叶亭既成赋》《桑乾夕》《李陵》《古意》《长安道》《楚妃怨》《橡叶亭》《山中》《六月十五夜雨》《桑乾涨》《早秋》《西山夜坐》《十八日夜雨见月》《桑乾河涨》《石佛村观瀑》《骑龙行(并序)》《赠贫士》《燕歌行》《行路难》《晚雨》《北涧观水入桑乾时久雨泛滥阴失经也》《连雨》《秋行役怀伯兄》《与山人》《蟋蟀曲》《山寺月》《山居》《陈弢庵太傅入山来访》《和叔明弟连雨韵》《从军行》《屋漏》《永夜》《述怀》《故园得嫂氏蕴香斋遗诗》《西山》《秋日西山望》《晚晴》《立秋》《登台》《七月十二日北坛见月》《七月十四月》《闻长沙水涨寄海印上人》《秋日寄伯兄》《塞上马二首》《塞上曲》《夜雨》《忆清河二旗村居(并序)》《西山秋夜》《悲长安》。〔4〕除《故园得嫂氏蕴香斋遗诗》一首关乎城中,余则多为“西山行踪”。是年,雨水充沛,山涧流瀑,桑乾河因久雨而泛滥。溥氏游居西山,卧林观瀑,多“苏武终年拥节旄”之悲。《故园得嫂氏蕴香斋遗诗》虽与萃锦园有关,亦非移居之诗:“翟服流文采,鱼轩遂不归。何年华表鹤,能向故城飞。一诵怀明德,千行泪满衣。魏舒八百户,犹得奉甘肥。”〔5〕就诗意而言,“鱼轩遂不归”“能向故城飞”暗示此时尚未归城。所谓“故园得书”,应与恭王府花园——萃锦园的修葺有关。关于葺园一事,溥氏曾于1935年向来访的袁思亮言及。袁氏依其所闻作《萃锦园介寿记》一文,叙溥儒、溥僡兄弟二人为母祝寿之前因后果。其中,有涉故园修整而后迁居之事:“吾母挈之避村舍中,期年遂居西山戒台寺。脱簪珥贸衣食,日督吾兄弟于学。如是者盖十有二年,始稍葺故邸后园,而归居焉。”〔6〕据此,“故园得书”应指萃锦园修葺过程中整理出的书籍。
《秋日将出山感怀》后第三首为《城中寄弟》:“知汝栖云水,犹能对万山。乾坤秋气肃,岩穴布衣闲。去国悲寒雨,归家尚苦颜。将心寄孤鹤,何日更西还。”〔7〕“归家仍去国”的悲苦之情,似乎是溥心畬移居之始的真实写照。纵观溥氏甲子夏秋之际的诗篇,虽有西山盛景相伴,内心挥之不去的却是“故国之思”。即便归居故里,这种情绪仍未得到慰藉。《城中寄弟》后有关返居萃锦园的尚有《归家》:“我似清秋燕,归飞入旧家。高台吹木叶,古井落寒花。夜雨愁中集,青山梦外斜。柴门无一客,还种故侯瓜。”〔8〕《故园》:“乱后山河改,荒园万木中。到家如逆旅,客泪散秋风。落月空梁白,寒花折槛红。归来对松竹,凋谢意无穷。”〔9〕乱后旧园,雨夜凋谢,故侯家园如同客舍,诗意极尽清冷哀怨,折射出这位旧王孙的“家国之痛”。辛亥避居西山十数载,虽世事动荡,却能获得山林采薇的精神调节。归居城中,意味着“不食周粟”的自我屏障面对某种程度的消解。加之“荒园万木”的眼前景,徒生“何日更西还”之慨,亦是合情。当然,归城一方面失去山野清静,不得不面对世事俗务;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群体活动的身份认同。作为逊清宗室之溥心畬,是遗民圈乐于交往的对象。故而,萃锦园很快在重阳节迎来盛大的雅集活动,诸多逊清遗老聚于恭王旧邸,宴饮赋诗。这次聚会,拉开了此后萃锦园十多年遗民雅集的序幕。王府花园就此成为“心怀故国者”的活动中心之一。大批从逝去的王朝走来的旧文人,在旧王孙堂前屋后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感时伤春的酬唱之曲。溥心畬,也在这些活动中寻到身为遗民的情感寄托。诚如甲子重阳聚会之名单,皆硕老长者,如陈宝琛〔10〕、朱益藩〔11〕、罗振玉〔12〕、王国维〔13〕等。是日,溥氏感念诸老,作《九日园中与陈弢庵太傅朱艾卿少保罗叔韫王静盦徵君潘惠盦孝廉雅集赋诗》:“凉风偏八极,白露明苍苍。雝雝云中雁,振翮东南翔。归飞越明泽,音响何哀伤。幽赏永今夕,奈此三径荒。高楼何迢迢,今为鸟鼠堂。仰观青天际,浮云互低昂。所贵见君子,斗酒非馨香。嘉会有终极,令德昭不忘。”〔14〕
从《秋日将出山感怀》到“九日(重阳)之聚”,表明溥心畬返城的时间应为甲子之秋,与姑母春日之寿构不成因果关系。那么,为何多年后旧王孙回忆往昔时,却将两者表述为因果关系?只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隐情?回答这一问题,萃锦园首次雅集中的陈宝琛似乎是一个有趣的突破口。因为溥心畬甲子夏秋间作于西山的组诗中,有一首《陈弢庵太傅入山来访》。
二
《陈弢庵太傅入山来访》是一首溥心畬常见风格的五律:“疏林带寒雨,空山响秋叶。泛泛广川流,凄凄晚风入。山中岁云暮,深宵客愁集。繁星鑑方沼,露湛凉簟湿。赖兹端忧辰,喜与嘉宾接。”〔15〕值得注意的是,溥氏用以修饰“嘉宾”到访的时间为“端忧”。何谓端忧?闲适之中的愁闷。闲适好解,西山隐居的生活自然是闲适的。那愁闷从何而来?且为何强调陈宝琛来时自己正这般愁闷?陈氏贵为帝师,所带之“喜”为何?当然,旧王孙与溥仪老师的山中会晤,具体言谈已然消散,无从考证。然大致方向却有迹可循。此前一年,溥心畬在城中与陈宝琛话别,作《归山别陈太傅》一首:“猿鹤频招隐,衡门去更迟。惭无刘向疏,空叠屈原辞(余癸亥二月出山,作《齐古赋》见志)。报国孤臣事,微才圣主知。时危思尽节,敢与昔贤期。”〔16〕该诗在《西山集》中出现在《癸亥七月西山怀海印上人》与《挽张忠武公》之间,张勋(谥号“忠武”)逝世于1923年9月11日(癸亥八月初一)。以诗文时序之编排判断,别宝琛归山的时间应在癸亥七月间。这些信息,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事实:甲子移居萃锦园的前一年,溥心畬曾多次往返于西山、城内。二月出山,作《齐古赋》;七月前归山,作《癸亥七月西山怀海印上人》;七月再度入城,继而与陈宝琛话别归山。有趣的是,癸亥四月十五日,陈宝琛曾有戒台寺之行,并作《四月十五日夜同颖生看月戒台寺(癸亥)》,〔17〕未言及居于戒台寺的溥心畬。此时,旧王孙应该“出山未归”,故而无法出现在宝琛的纪游中,却意外出现在《赐砚斋日记》中:“(四月)廿八日入直,见恭忠亲王孙溥儒,书气盎然,人亦敦厚,远胜于称修诸人,侊杰佳更无论矣。”〔18〕显然,溥氏进城见谒了溥仪,出现在故宫的小朝堂。据此,重读《归山别陈太傅》中的“报国孤臣事,微才圣主知”,可隐约判断这位旧王孙的“心之所系”。
或许“心有所系”,溥心畬才发出“惭无刘向疏,空叠屈原辞”的自比。这说明作《齐古赋》前后,溥氏负有某种政治理想,故有“时危思尽节,敢与昔贤期”的执手话别。当然,言下之“尽节”,并非王朝更迭时的惨烈行径。此时,辛亥已过十数载,在“清室优待条款”庇护下,紫禁城依旧延续大清王朝的礼仪典章,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国中国”,成为“旧臣”的精神寄托。他们进出故宫,如往返“帝制”与“民主”的不同时空。因此,身为遗民的满清旧臣,并未丧失“国家认同”的主体投射。溥仪的存在、故宫的存在,不仅是心理慰藉,更是心理暗示。于是,众多“孤臣”围绕依旧贵为天子的溥仪,成为民初北京城的一道风景。身为宗室的溥心畬,想来不例外。然而,一方面“国”之仍存,一方面复“国”无望,聚集在紫禁城里的皇帝、臣工丧失“天下事”后,充满焦虑与无奈,只能“过家家”般地延续旧日朝堂曾经的纷争。癸亥出山的溥心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平静,却不太平的小朝廷。诸如,就在他与陈宝琛话别之际(阴历七月间、阳历8月下旬),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别后左目大肿,因肝火发动,并左耳亦不适。颍川对敝宗人一节,狂悖极矣,弟意照公来书所言(去就一节),尚须与敝宗人就商,弟意即欲决去,前次之文,亦可托心畬代呈,并将不可相处之意告知心畬,托心畬代言。至尊处,谓假得请乃可行,不可微服迳去也。楫先言敝宗人非面上不可,此出自渠之公道与热忱(此亦可不必),然弟意敝宗人之文,亦可由心畬上达,不必由颍川,望将鄙意代陈。一目作书,草率尤甚。”〔19〕
信札虽短,却仿佛“溥陈道别”的画外音,饱含信息。言中“敝宗人”即溥心畬岳父升允,此时正与陈宝琛激烈冲突(颍川对敝宗人一节,狂悖极矣)。陈氏何为?以致罗振玉如此愤慨?同期另一封信札为后世揭开了谜底:“在都闻颍川阻敝宗入内之事,愤此老之敢于朋比为恶,肝气横决,归而病目与耳,苦闷不能视物者三四日,延医诊治已渐愈,而耳疮未平(滞下愈否,珍卫为盼,暑中外出,以马车为稍好,此等小费,不可惜也)。昨晨敝宗人来见,尚勉强出见,知已面觐,出示疏稿,读至末数语,为之哑然。至夕而得手示,知颍川云云,弄人者亦为人所弄,天道好还,为之称快……”〔20〕结合上一封信中“楫先言敝宗人非面上不可”看,陈宝琛阻止升允“入内”,被罗振玉视为“朋比为恶”。当然,结果是升允最终得以“面觐”,罗振玉甚为欣慰,并嘲笑陈宝琛“弄人者亦为人所弄”。陈宝琛、罗振玉、王国维、升允等,皆溥仪朝堂的肱股之臣,具体纷争已然无考,想来不过是为君分忧的意见不同。那么,身陷耆老之争的晚辈,溥心畬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依罗氏书信所显,这位旧王孙起到了穿梭往来的信使作用,一些不便直言的皆“托心畬代言”。至于信使工作成效如何,却无从得知。
种种迹象表明,甲子归城的前一年,癸亥中的溥心畬身陷溥仪朝堂的诸多事宜,且与罗、陈诸方保持了良好的沟通。或许在溥氏看来,促进这些硕儒耆老的团结也是“时危思尽节”的重要内容。但溥心畬能多大程度影响他们?奔波于长者间的旧王孙,恐怕只能发出“微才圣主知”的感慨。癸亥归山的溥心畬,内心是否因此深感无力?《归山别陈太傅》后一首诗为癸亥重阳所作《九日》:“九日登高望,边声入塞深。天风催短景,寒叶响空林。枫乱千家雨,秋惊万里心。古人如揽结,高卧散幽襟。”〔21〕“揽结”一词本为“采摘系结”,于此尚喻“结交”;“高卧”一词于“悠闲安卧”之外,亦有“隐居不仕”之意。远离朝堂,“秋惊万里心”的溥心畬在癸亥重阳登高处,似应落寞如秋。落寞,是遗民必然的情绪。即便没有罗、陈之争,幽居西山的溥心畬重阳登高时,总会不免惆怅,不免故国之思。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来自历史深处的传说——首阳采薇,不仅感召了理想的预期,同时也塑造了情绪的自我催眠。王朝更迭时,他们因此成为新秩序的免疫者,充满情感的不适。
对现实生活的不适感,是经典话语塑造“文人主体”的大概率副产品。传统社会结构中,文人被塑造为引领者、楷模,需要道德上的“超世俗”以建立自身形象的合法性。身处世俗却不得不超越世俗,成为文人必须面对的生存悖论:疲于应付现实的同时,又要具有“超越现实”的品格、德性。否则,儒家世界提供的“道统”中,他们就不再具备日常秩序的建构者身份,并丧失自身的社会化功能与价值。因此,生存现实与理想塑造是中国文人先天的矛盾结构,也自然带来情感世界中“不适感”的时常出现。与之相应,两种充满隐喻色彩的植物——菊花与薇蕨,分别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周粟”的道德事件为内涵,针对“不适感”展开调节。其实,与其说是调节,莫不如说是催眠——假借菊花、薇蕨的前贤往事,寻找安守落寞的内心力量。表面看,菊花、薇蕨都代表了远离世俗、避居山林,但内在逻辑却完全不同。前者是常规状态下的隐逸行为,单纯指向世俗日常,塑造文人“骄傲”的道德操守——不屑于凡尘龌龊的清高;后者是特定条件下自我放逐,针对政权更迭的动荡岁月,塑造文人“悲壮”的道德操守——忠于前朝旧主的坚忍。从某种角度看,菊花是一种“出世”象征,而薇蕨则是假借“出世”以“入世”。因此,薇蕨代表的遗民,生存体验的“不适感”很难获得“采菊东篱下”的潇洒,更多的是沉重的漂泊与悲怆。晚清遗民,相对过去尤为如此。因清帝退位并非前朝旧事可比——以和平方式结束千年帝制,是曾经的政治合法性的终结者。这便使晚清遗民成为历代遗民中最特殊的群体,宛如失重的政治孤儿,面对一个无法再以“既有经验”获取“自洽身份”的尴尬局面。并且,吊诡处还在于,象征过去的皇城乃至皇帝仍然存在,仿佛消失了的旧王朝向他们打开一扇时空之门,以物质方式吸附着他们的忠贞。于是,他们连自我放逐权都丧失了,成为漂泊在新时代的陈旧曲目。晚清遗民的悲怆正在此:他们的“薇蕨”没有纲常社会之伦理需求,因而借以塑造的“道德操守”无法在新时代成为楷模。加之大清政权尚苟延于紫禁城,使他们既无法“入世”也无法“出世”,仿佛阴阳两界游荡的魂魄。
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除了惶恐与彷徨,晚清遗民还残存着匡复河山的微渺希望。正是这微渺之望,使他们难以“高卧散幽襟”,也更容易走进现实俗务,围绕“匡复”的精神领袖——溥仪展开诸多人事纠缠。介入罗、陈之争的溥心畬,即如此。癸亥归山后,他并未获得“山林解脱”。相反,城中动向时刻牵引他的悲欢喜忧。诸如,听闻张勋去世作《挽张忠武公》:“雪紼悲风起,长江洒泪深。苍凉万夫泣,惨淡大星沉。圣主褒忠诏,孤臣下地心。黄河终不渡,遗恨白云岑。”〔22〕辫子军领袖张勋在后世描述中并非正面人物。他主导的“复辟”常被视作闹剧,成为史家嘲讽对象。但对大清遗民而言,张勋形象就完全不一样了。1923年9月11日(癸亥八月初一),张勋去世在遗民圈引发无限哀思。翻阅他们诗文集,大多出现“挽张忠武公”之作。想来正常,张勋面对新时代的不合时宜,恰是晚清遗民的自我投射。看似荒唐的“复辟”在遗民眼中却是“匡复”之义,不仅得到广泛认同,还是微渺之望的闪烁星辰。如此一位忠贞之士的逝世,自然成为“惨淡大星沉”,以致“遗恨”不已。或可说,溥氏之悲不仅指向张勋之死,亦是内心复国难酬的哀愁。
身处城外的溥心畬,心为城中而动;城中人对溥氏,亦有难忘之情。因恭亲王孙的身份,溥心畬在遗民圈中具有加持的光芒,也因此有着政治上天然价值。癸亥岁末(阳历12月15日),罗振玉对升允是否入山,问之甚切:“素入对后,所言如何?而高密所言如何?请示其略。素已入山否?念念。”〔23〕言中,素(庵)即升允,溥心畬的岳父;高密本指汉代郑玄,这里指郑孝胥。罗氏所问王国维者,当是此前言及的面圣之事。时罗振玉身在天津,王国维身处紫禁城。罗氏希望从亲家翁处获知升允觐见溥仪的结果如何,同时也想了解郑孝胥的情况。一句“素已入山否”显现了两点信息:一者罗振玉、升允曾有入山之约;一者入山发生在北京,故需向北京的王国维询问。那么,所入之山为何山?所见之人为何人?就现有材料分析,升允在北京最大可能就是入西山,会见自己的女婿溥心畬。此后数日(1924年1月1日),溥心畬即有天津拜会罗振玉的行踪。似乎印证了升允入山,就是为了完成罗振玉之托,促成罗氏与旧王孙见面。
罗振玉对此次会面极为满意,第二天致信王国维:“日磾之奉新命,果能遂远之否(倘就此职,亦必闹笑话)?高密之诗与日磾之泄漏上纶,同一荒谬。公移书诘责,至佩至佩。弟与素公言,我辈在背后议其短长,不如且破釜沉舟加以警告,警告不听,则朋友之道已尽,为鸣鼓之攻可也。素甚谓然。惟明道、紫阳今日议论尚如此,可谓全无脑筋(去冬素老令坦上书言事,紫阳亦阻不令上达,不知果何心也),与彼方阴结外邪,实为此次粗厉结果之导线,故非谋中立正大之人才,不足以弭三方之弊(此一方真所谓三峰并峙,无可轩轾)。颠倒思维,舍名声太大者,实无弟二人,而中间斡旋,须得有力者。昨素老快婿在此鬯谈,其人有肝胆有知识,我辈所言,一一均能领会。现为稷下之游,弟劝其入觐,并上封事,具结厶上公为之助(闻此人甚要好),或有万一之望。尊意以为如何?近日若有所闻,尚希续示。”〔24〕收获此信不久,王国维回函:“前晚一函,想达左右。昨奉书,敬悉一切。顷阅报纸,见彼方公府秘书厅函件,剪附尊览。高密于此事已栽一大跟兜,稍有人心必须自退以谢天下,加以天怒人怨,恐不久即不能站脚。日磾亦必随之而倒。故前日素意俟其自败,不必加功(维意或令心畬入城一次,面陈一切。素答如此甚老成之见,亦是自留余地)。窃意高密减政之策,本不期实行,但以掩人耳目,其大计划既败,则亦自必求去(对素言不行则去,素即赞之)。目下急务在善后之策。元气大伤之后,外御风寒,内调肺腑,在在为难。库书一项,将来只有公开一法,以免攘夺,此则高密所断送者也。”〔25〕
两札所涉之人,除前述者外,日磾原为汉代金日磾,这里指金梁;厶上公则指溥仪岳父荣源。另,札中“明道”与朱益藩的隐称“紫阳”并列,应为庄士敦代称。〔26〕“惟明道、紫阳今日议论尚如此”或可印证《郑孝胥日记》癸亥十二月初六日(1924年1月11日)所记:“八时至神武门,十时召见,十一时二刻始下。奏保金梁、佟济煦、袁金凯,及发印《四库全书》。弢庵邀饭于庆和堂,庄志道士敦、朱艾卿皆在坐。”〔27〕这一天,是郑孝胥刚到北京的第三天。此前一天的日记云:“弢庵来。贻书来。梦旦来书,言缩印《四库全书》事,以书示弢庵,且言:‘此举宜由皇室发起。’”〔28〕由此推见1月11日聚会的四人——郑孝胥、陈宝琛、庄士敦、朱益藩,正是支持《四库全书》(清宫内务府文渊阁本)交商务印书馆影印的一派。从罗振玉1月2日致王国维的信札来看,罗、王及升允等人对此并不支持,且对庄士敦、朱益藩的议论(郑孝胥此时尚未来北京)颇为不满。就札中谈及“心畬来访并畅谈”,对“我辈所言,一一均能领会”看,溥心畬对郑孝胥一派亦不支持。不支持原因何在?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札“库书一项,将来只有公开一法,以免攘夺”一句,透露了罗、王派对此事的担心——恐为攘夺。虽《四库全书》外运之事,农历年后方才实操运作,但王氏预测却成为现实:“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到当局的阻止,把书全部扣下了。”〔29〕
《四库全书》一事之外,郑孝胥入宫的主要职责是整顿内务府。当时,溥仪朝堂虽保留清廷曾经的“建制”,却无国事可理:“这些新增加的辫子们来到紫禁城里,本来没有别的事,除了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之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登记上账。”〔30〕相对很多强调礼制祖法、空言复辟的条陈密奏,金梁、郑孝胥力主从内务府整顿入手的计划更务实,也获得了溥仪的认可:“金梁当了内务府大臣之后,又有奏折提出了所谓‘自保自养二策’,他说‘自养以理财为主,当从裁减入手,自保以得人为主,当从延揽入手’。‘裁减之法,有应裁弊者,有应裁人者,有应裁款者’,总之,是先从内务府整顿着手。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做法。”〔31〕“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并提出了比金梁的条陈更具体的整顿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要减去,不仅能杜绝流失,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能够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内务大臣,并且‘管印钥’,为内务府大臣之首席。”〔32〕郑孝胥主导的减政计划,显然不为王、罗认可。虽王国维言下“高密于此事已栽一大跟兜”之具体,已不可考。但王氏看来,郑减政计划并非真目的,而是一种幌子——“窃意高密减政之策,本不期实行,但以掩人耳目”。基于此,罗、王试图“破釜沉舟加以警告,警告不听,则朋友之道已尽,为鸣鼓之攻可也”。如此争斗下,作为“素老”女婿的溥心畬似乎没有太多选择。故而,王国维才有“令心畬入城一次,面陈一切”的建议。升允对这个建议亦甚赞同,认为是“老成之见,亦是自留余地”。何谓“自留余地”?即借助溥心畬特殊的宗室身份觐见溥仪面陈一切,可避免与郑、金发生直接冲突,正是罗振玉所谓“中间斡旋,须得有力者”。由此可见,溥心畬在罗、王眼中,能在冲突中起到很大的缓冲作用,既能传达意见,又避免了与对方的矛盾激化。因此,溥心畬癸亥遭遇挫折归山后,12月升允入山再次说服他出山,并促成溥氏1924年1月1日前往天津拜会罗振玉。显然,罗氏对“拜会”结果很满意,认为溥心畬对“我辈所言”,“一一均能领会”。
三
前有陈宝琛后有郑孝胥,从癸亥到甲子,溥心畬无法回避溥仪朝堂的诸老之争。这场纷争中,罗振玉等人与陈宝琛的矛盾似乎更为空泛,而与郑孝胥却有具体事务之分歧;陈宝琛支持郑孝胥,但溥心畬与陈宝琛又私交甚好,故三方关系不断发生微妙波动。升允入山劝说溥心畬时,似乎也带来弢庵试图入山访见之意。李宗侗先生曾在《敬悼溥心畬大师——兼述清末醇王对恭王政争的内幕》一文后,附录一封心畬致弢庵的信:“弢庵太傅:未见君子,悠悠我思。昨晤升公,知太傅有辱临之志,良喜。然儒将游济南,且登历山,访舜祠,揽鹊华,俯黄河,浃辰始归,恐违邂逅,以忧执事,不敢不告。溥儒顿首。”〔33〕对此信,李宗侗先生判断:“另附心畬致陈弢庵(宝琛)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文笔之优美及其字体的高逸。这函大约是民国十八年左右的。弢庵是陈宝琛,字伯潜,老年方以此自号。”〔34〕确认该函为“民国十八年左右”的理由,除陈宝琛晚号弢庵外并无其他依据。然查溥心畬1929年左右诗文,未见相关纪游。且,前述甲子夏秋作于西山的《陈弢庵太傅入山来访》,即以“弢庵太傅”称呼陈宝琛,〔35〕故,所谓晚号弢庵也不能支持该信为1929年左右所写。结合信札内容与溥心畬行踪,此信写于癸亥冬日升允入山后一日,溥心畬前往天津拜访罗振玉(并有“稷下之游”)前,更为合理。
“稷下之行”,除前引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1924年1月2日),《西山集》亦有相关纪游。“稷下”本指战国齐都临淄设立的学宫,此处应为“致陈宝琛信”所谓的“山东之游”。《西山集》卷三在《挽张忠武公》之后连续录《大明湖》《拜张勤果公祠》《经华不注山》《石门》《甲子鲁道中》五首:“台阁连青草,萧然罢胜游。空余历城水,犹带鹊华秋。坝古鱼龙合,天高汶泗流。还思杜陵客,愁望倚南楼。”(《大明湖》);“赛曲神弦响易悲,椒兰纷座雨如丝。行人酒酹祠前水,日晚灵风卷画旗。”(《拜张勤果公祠》);“高原飞鸟没,此地覆齐师。不异牵羊辱,终无介马驰。孤城秋草合,战垒野风悲。临眺多陈迹,斜阳卫水湄。”“空城下寒日,行役客中过。秋色生东亩,微霜已涉河。青山平野近,白骨战场多。韩厥翻知礼,临风发浩歌。”(《经华不注山》);“霜气惊边雁,秋风发石门。乱流传石坝,山雨洒寒村。波浪桑乾合,风云寨口昏。回车问亭长,欲酹旧征魂。”(《石门》);“碣石苍茫接岱宗,平原烟树晓葱茏。鲁王宫殿秋风里,汉帝旌旗返照中。白雁南飞云入塞,黄河东去水如虹。登封万骑无消息,玉检金泥恨不穷。”(《甲子东鲁道中》)。〔36〕1924年1月1日,天津拜会罗振玉后有“稷下之游”;出发前致信陈宝琛,言因“山东之行”而“恐违邂逅”。时间、地点均与本组纪游诗吻合。又,《甲子东鲁道中》时间为甲子,查该年除夕为1924年2月4日,故“稷下之行”应从1924年1月2日到2月初,为农历年前后。此时,溥伟奉嫡母居青岛,溥心畬还可能途中过青岛省亲并过年。〔37〕
稷下归来后月余,溥心畬进城参加姑母荣寿公主的寿诞(甲子二月二日,即1924年3月6日)。这件后来被描述为重要事件的“事”,彼时似乎波澜不惊。甚至当时的诗文写作中,几无任何踪影。相反,与祝寿无关却显现溥氏“心系城中”的,多表现为他与城中遗民的互动。诸如,年初因溥氏稷下之行而未能“邂逅”的陈宝琛,终于在他祝寿后“入山”相会。对此次弢庵太傅的“入山”,溥氏写下《陈弢庵太傅入山来访》一诗,并称之“赖兹端忧辰,喜与嘉宾接”。这首溥氏常见风格的五律,表述了弢庵之访恰逢其时:深宵客愁际,喜有嘉客到。而陈宝琛带来怎样的消息?具体言语,今天已无从知晓,但大意却可考辨。此年8月27日(七月廿七日),即陈宝琛“入山”前后,罗振玉在给王国维的信中写道:“素言上问高密为人,素对以言大而夸,作事凌乱无序,不循轨道,上笑而颔之。素又言,陈为我言,此次劝心畬入对,并与我言,将请上添入南书房,此亦与我卖好之一端。若彼赏识心畬,何必为我言之?素又言,与陈相处,固不必攀援,亦不必拒绝。并言静安深得此旨,我遇胡、陈邀我饮于后门,并邀静安作陪,静安已饭毕,亦来周旋。我以此是知静安为人,甚得中和也。弟戏谓此静安因陪老帅耳,素曰晚间静安来寓,亦饭罢复饭,此确是周旋我,午间确为应陈召。相与大笑。附书亦博公一笑。”〔38〕
此札乃罗振玉告知王国维从升允处获知的消息:既有上(溥仪)询问高密(郑孝胥)之事,亦有素相(升允)认为静安(王国维)深得交往弢庵之道。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陈太傅曾向升允表示“此次劝心畬入对”,更欲“将请上添入南书房”。所谓“入对”,即面觐溥仪。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弢庵太傅为何要劝旧王孙“入对”,但该信息正是陈宝琛入山拜访溥心畬的“注脚”。溥心畬“添入南书房”一事,后来不了了之。最终,“南书房拟添二人,一为罗某,一为柯某”。〔39〕然而,帝师陈宝琛的“劝说”与“态度”对身处山林而心系朝堂的旧王孙,无疑是一味振奋剂。尤为重要的是,“添入南书房”的提议,意味着溥心畬必须离开西山,迁居城内。成为溥仪朝堂的肱股之臣,对“惭无刘向疏,空叠屈原辞”的溥氏而言,定然有着很大诱惑。遗民深居山林,往往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城中已无效忠对象,“入城”通常会成为“食周粟”的象征,以致对遗民的“坚守”产生冲击。然而,陈宝琛可能的劝说中,“入城”不仅不再是身份“背叛”,反成为一种“效忠”,成为遗民之志的重要体现——因“报国心无改”而扶助“危难”旧帝。是故,无论是否真得“添入南书房”,因为溥仪的存在,因为大清的象征依然存在,放弃山林便具备了不同于历史既定经验的合法性。它不仅不会损害遗民操守,甚至还会助力遗民的自我期冀——“时危思尽节”。显然,这次西山会晤中,持重老臣弢庵太傅的“劝说”打动了大清宗室溥心畬,两人在“出山入对”的方向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或受陈宝琛的感召,写就《陈弢庵太傅入山来访》后不久,溥心畬又作了一首《从军行》:“幽州白沙寒,边霜折枯草。戍卒吹笳百战场,胡儿牧马萧关道。无定河边沙暗飞,单于昨夜解长围。偏师北逐烟尘绝,不击名王誓不还。”〔40〕《从军行》为乐府旧题,多表现边关疾苦。幽居西山的溥心畬虽遇国变,生活仍算安逸,未有沙场奔行的任何经历。一个文人逸士写作《从军行》,显然不是自我经验的“写实”,而是借助历史修辞抒发情感。溥氏此诗在意境上并无创造,基本是过去类似之诗的“言语重构”。有趣的是,发出“不击名王誓不还”的铿锵之音,对此时的溥心畬却是恰当、真实的。这种真实,源于情感的“真实”。即便没有实际经验,古人的边疆激昂依然点燃了文弱书生的情感共振,并借以抒发建功立业之宏愿。
退隐山林而独善其身,并非文人的最终目的,只是自我完善的不得已选择。条件允许下,入世兼济天下才是文人真正的理想。以儒者自期的溥心畬,自不例外。“少小受经史,望古希曾颜。上书慕忠节,怀兹中险艰。未能正吾君,惭愧归邱山。听泉林下风,策杖青崖间。孰事危不持,乃以求自宽。恨无古人义,高山安可攀。”〔41〕这首与《从军行》同期所作的《述怀》,真实再现了溥心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二元心理结构。隐居西山十三年,溥心畬虽然不再是大清治下的王府贵胄,却也是身处与现实动荡相对隔绝的“保温箱”。得益其祖恭亲王对戒台寺的捐助,青少年的溥心畬在深山古刹保持了一种宁静而悠缓的生活状态,并因此浸泡在经典的旧式教育中。与山外城中截然不同,戒台寺的钟声依旧延续着古老帝国迟缓的节奏,溥心畬甚至没有溥仪在故宫中接触新学的机会。当然,逐渐地,他自身也不再具有针对新学的需求,并习惯于古典形态的知识结构分配“自我”的存在秩序,乃至情感塑造。从某种角度看,溥心畬完美躲避了一战前后的世事剧变,也完美回避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岁月。五四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等耳熟能详的历史名词,对这位旧王孙是如此遥远、陌生。他的精神世界中,因“少小受经史”而期望成为孔门贤德——曾颜(曾参、颜回),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仿佛来自并不久远的时代的“活化石”。亦因于此,他成为遗老群体中的少壮派,在耆老的纷争中往返奔波。所谓“未能正吾君,惭愧归邱山”,一方面是他无力于现实的感怀,一方面也是他延续经典文人心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的无奈怅惋。
归于邱山是因为“未能正吾君”。那么当陈宝琛带来“入对于君”的建议时,出山返城便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之一。或因于此,甲子成为溥心畬一生行径的节点。这年秋日,他结束了自己长达十三年的西山“隐居”,返回城中故园——恭王府萃锦园。对这段并非主动规划的“隐居”,溥心畬内心情感是复杂的,故在别离前作《忆清河二旗村居(并序)》:“岁次辛亥,京师乱,余年十六,避兵出奔,止是乡焉。自徂西山,十三年矣。感今伤昔,作为是诗。昔我居东野,孤村背长川。稚子出负薪,雪中炊寒烟。少小读经史,未解希前贤。今闻草堂木,千寻参青天。浮云变无极,寒暑忽代迁。人生岂不化,百忧相率牵。不见昔人墓,今人犁为田。”〔42〕因避乱而来此山中,今为“君”故再别离。然山中数日,人间百年。所谓“浮云变无极,寒暑忽代迁”的悲歌,与其说是针对世事沧桑,不如说是针对自己“出世非己愿”“入世又未卜”的命运状态。“今闻草堂木,千寻参青天”,恰是“感今伤昔”的情绪之“眼”。在出世、入世间,溥心畬所代表的晚清遗民充满了命运多舛的自我悼怜,曾经行之有效的“出入”二元结构,在新时代已然失效。他们没有新的方式调节自我,只能继续“少小读经史”的虚拟优越感,支撑自己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入山”如此,“出山”亦然。唯因于此,即便“出山”也难以获得“入世”之笃定,会不断产生情绪上对“入山”的回望。“去国悲寒雨,归家尚苦颜。将心寄孤鹤,何日更西还。”刚刚入城所写之《城中寄弟》,真实显现了这种在“出”“入”之间的往复与惆怅。
传统文人的“出”“入”是一种超越、领导世俗的主体建构行为,具有儒家世界的现实基础。也因此,他们才能获得社会的正向反馈,并塑造心理上的自我优越。然而,晚清遗民面对的世界却是“儒家系统”逐渐崩溃的时代。无论是“以西补中”的温和改良,还是“打倒孔家店”的激进革命,文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主体建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并趋于瓦解。“出”以自我标榜、“进”以建功立业,很难获得社会的积极响应,相反却开始成为“腐儒”象征。虽然新生的“科学”“民主”没有塑造出全新的国民心理,却使旧系统发生了价值观的紊乱、失效。中国,至此进入大过渡时代,新旧处于交糅混杂的状态,双方都无力重构一个稳定、统一的“家国天下”,都逐渐成为脱离现实问题的“新潮流”,抑或“旧染缸”。或可说,进入20世纪以来,无论旧式文人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面对一个巨大的陷阱:思想最终服务于具体问题,成为现实的工具。他们很难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建立有效的“通道”。“形而上”的思想因此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成为空洞的宣传口号——需要时则被利用,不需要时则弃若敝履。这种对待思想的功利化趋势,自然是躲在儒学外套下的晚清遗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想明白的。但他们直观可感的是,“入世兼济天下”的路径似乎消失了。
“兼济天下”是传统儒学思想走向现实的“通道”,是从纲常道统之学走向经世济用之学的“通道”。借助于此,文人将自己的“形而上”嫁接到了“形而下”,成为社会秩序的领导者。然而对晚清遗民而言,这条“通道”忽然消失了。一战风云、“五四”救亡、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儒家世界观从未面对的新问题,使晚清遗民的“思想”失去了现实践行的场域。曾经引以为傲的“少小受经史”一夜间成为“无用之学”,成为“自我假想”与“真实世界”之间的一堵高墙,屏蔽了他们走向现实的能力。他们仿佛是开在盛夏的雪莲,依旧晶莹剔透,却那般不合时宜。丧失先辈文人对现实的塑造力,晚清遗民的“儒学”无力解决当下问题,“入世”空间也相应萎缩,“兼济天下”逐渐成为“效忠旧君”的代名词。甲子“出山”的溥心畬,正如此。
溥儒 山水 绢本设色 约1924 故宫博物院藏
四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溥心畬“臣”字款作品,〔43〕折射了他的“出山入世”不过是“效忠旧君”的一种方式。这件绢本《山水》以典型马夏笔法描绘了一处山涧小景:类似《踏歌图》的高耸垒崖,间有松枫之木,白衣高士倚卧石上,俯望涧流。就主题而言,这是表达“隐逸”的常见题材——山涧深住、松下隐居、清泉濯足等。画无题识,右下处落名款“臣溥儒恭画”,钤白文印“溥儒”。就“臣字款”及“恭画”而言,看似平常的隐逸之作因赠送对象变得丰富起来。显然,这是一幅用心构思、创作的“进献”之作,非随意临仿。画中凋零的红枫暗示了晚秋时节;挺拔之松与白衣高士构成精神互文——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山涧清流,亦是高洁之志的隐喻。问题是,溥心畬为何营造如此之境奉于溥仪?作为大清国仍然存在的象征,溥仪是不需要“隐逸”的。相反,在“臣民”心中,他必须留在紫禁城成为一种精神寄托。故而,溥仪的出国计划才屡遭挫折。那么,溥心畬为何要将一幅隐逸之图献给并不要“隐逸”的溥仪?基于“进献”的严肃性,图像选用不是随意的。尤其,这些图像共同指向历史深处的“文人气节”,暗示了“创作”是有着明确的意图。
或许在溥仪看来,这件作品应该构不成珍贵的“物件价值”,它更像一种情谊的象征。溥仪与溥心畬有着怎样的情谊?他们虽是堂兄弟,但恭亲王一支因与“帝位”较近(溥伟甚至有觊觎之心),故与溥仪关系并不亲密。溥心畬是以臣子身份向溥仪进献一件自己的画作。款中“臣”“恭”两字,正是该行为的直观显现。此时,“溥仪”在溥心畬心中仍是大清遗民“君国一体”的施动对象,并非血缘关系的兄弟。面对如此一位“施动对象”,史上常见的隐逸题材因恭敬的绘画行为而成为“暗语”——画家本人正如所画之白衣高士,在山林崖涧中饮泉采薇。所以,这幅作品与其说是献给皇上的礼物,不如说是臣子忠贞的自我表白,表白一种君君臣臣的伦理情谊。当然,这并非针对溥仪个人,而是针对溥心畬心中仍存的“大清国”——因溥仪存在而存在。因此,山涧深住、松下隐居、清泉濯足等题材在画面中成为遗民情操的喻体,向画作接受者塑造了一个画外主体——西山逸士溥儒。如果说,这是溥心畬对个人身份的自我想象,那么进献对象溥仪则是“想象”的保证与前提。正因为有溥仪这样一位旧君的存在,作为“臣子”的溥心畬才能将一幅常见题材转换为“报国孤臣事,微才圣主知”的自我感动,并构建“君圣臣贤”的意义空间。或可说,这张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图像,其意义源自画家与预设观众(溥仪)的关系。它不是一幅为“绘画史叙事逻辑”创作的作品。甚至,它在被创作的过程中都不被视作“艺术概念”控制下的图像生产。之所以选择这些图像,仅因为它能恰当表明政治立场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抒发——精心构思的画作犹如一幅图像化了的《陈情表》,向“效忠对象”娓娓道来。
这件臣款山水之所以出现在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目录,应是溥心畬于溥仪出宫(1924年)前所献,未被带出而留于宫中。此后,文物南迁的动荡岁月中,它“一如既往”地不被重视,便一直保存在北京的库房里。仿佛被人遗忘的“曲目”,它躲在历史深处孤独地演奏画家的内心独白。这份“独白”的历史际遇,俨然是晚清遗民的命运隐喻:虽然倾情出演了自己的角色,却终究是舞台上无关紧要的过客——于寂寥中自我催眠,于寂寥中黯然退场。他们无力参与20世纪正在发生的现实,诸如“民族国家”概念的产生,仍然抱着旧的“天下”体系理解“家国之忠”,并围绕效忠对象——溥仪展开入世的抱负、理想。显然,结果不尽人意,如同这件臣款山水被闲抛闲置,在尘封的岁月中褪色凋零,无人问津。当然,如此评判有些“后世之明”的残忍。身为当事人的晚清遗民,无需服务于后世之历史逻辑,他们关注的是自身的历史渊源。也即,后世历史可以不选择他们,他们同样也可以不选择正在发生的混杂现实,坚持从既有历史中获取的经验、概念乃至价值观。围绕“国家”的想象,正如此。
注释:
〔1〕《西山集》为溥心畬早年诗集,现天津图书馆藏有自书三卷本(以行楷书于清閟阁造笺),当为陈隽甫所购《西山集》(石印本)的手稿本。陈氏所购《西山集》为手书石印三卷本中的“一卷”。据心畬题跋可知当时印制不过百册,世事动荡而散佚殆尽,今已不见三卷全本。陈购溥题本,现为台湾董良硕先生所藏,亦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1993年(民国八十二年六月)所编《溥心畬先生诗文集》(上)中《西山集卷一·民国十四年自书本》的底本。溥题内容,见于《溥心畬先生诗文集》(上)所收《西山集卷一·民国十四年自书本》第40页。另,陈隽甫毕业于北平艺专,师从溥心畬。擅长画虎,与许麟庐、田世光等为同学,并与同窗吴咏香结为伉俪。1947年在香港举办夫妻联展后赴台定居,设欧波馆课徒作画,曾任教于台北师大美术系。
〔2〕《溥心畬学历自述》流传甚广,版本虽有细微之差,然内容基本一致。其中,张目寒藏心畬书《心畬学历自述》(后有马寿华注语)曾发表于詹前裕著述,本文以此为本。詹前裕《(台湾近现代水墨画大系)溥心畬——复古的文人逸士》,艺术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3〕《寒玉堂集》是溥心畬《西山集》之后的一本自编诗集,现有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溥氏自书抄本。该抄本收录之诗自1915年至1942年,跨溥氏青壮年时期。本文中《西山集》《寒玉堂集》的“引文”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溥儒集》,并分别对校于天津图书馆藏本、河北师范大学藏本。《秋日将出山感怀》一诗见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甲子秋日将出山感怀》一诗见溥儒《寒玉堂集》(卷上),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
〔4〕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26页。《西山集》排序基本以时间为线,故所列篇目大致可以确定为甲子夏秋间所作。其中,《骑龙行》序亦有明确甲子纪年。现将能显现“西山之居”的诗作依次录如下:“石梁闷幽景,寒岩迈孤往。草木湿苍翠,泉流激清响。白云媚幽姿,空山自俯仰。感此鸣素琴,何求知音赏。”(《甲子夏六月山雨连夕岩壑出云坐涧桥观瀑清风时来山翠流滴即景赋此》);“白云何所止,止于幽巘阴。前楹架虚涧,峰壑窗前临。岂不惮阻险,爱此风雨深。有客缅高洁,遗我弦外音。忘言对溪石,流目瞩高岑。陵谷忽已改,岁月方骎骎。我有杯中物,慰此尘外心。”(《西山石多橡树作橡叶亭既成赋》);“秋风发长洲,野火生前浦。萧萧贾客愁,暮入寒山雨。”(《桑乾夕》);“白云起幽壑,徘徊岩石间。回风一披拂,忽焉满西山。抱琴坐深树,长吟日夕闲。谷口下黄叶,浩然归闭关。”(《山中》);“昨夜桑乾渡,风波舣客舟。君看盘峡日,犹似下黄牛。”(《桑乾涨》);“山迥清残暑,西风欲授衣。星移天宇净,云淡露华稀。江汉蟾蜍病,河梁乌鹊飞。凄凄对修夜,摇落客心违。”(《西山夜坐》);“始霁西山雨,今登北渚楼。壮心随骥马,幽梦讬沙鸥。秋色前宵满,清光永夜浮。故园空不见,星汉正南流。”(《十八日夜雨见月》);“岩壑昼蒙蒙,桑乾宿雾中。黄昏杂风雨,古坝出鱼龙。率土怀周德,神州失禹功。郭门瞻息壤,搔首恨无穷。”(《桑乾河涨》);“山馆连斜景,苍然万壑阴。岭云生石壁,涧水出幽林。暮雨高城雁,秋风少妇砧。上方归路晚,钟磬隔烟深。”(《石佛村观瀑》);“甲子夏,桑乾水涨,有兄弟入水求木者。兄跃乘焉,俯有鳞甲,乃龙也。知所不免,顾弟曰:“善事母,勿念我。”龙遽掉其尾,掷其人数丈。赋诗以志。河伯夜战逃天吴,阴风卷地成江湖。北方之强有兄弟,提刀入水非凡徒。截流攀木见鳞甲,危哉已探骊龙珠。伯也掷刀向天指,小人有母何敢死。匹夫一呼苍龙惊,拔浪掉尾如雷鸣。须臾夭矫不可见,烈风盘盘天柱倾。昔者包牺之王天下龙出图,始制文字垂圣谟。又闻黄帝升天骑赤龙,遗迹空有乌号弓。龙者神物不知其变化,至诚之道无乃能感通。洪波荡荡鼋鼍舞,云冥冥兮风昼怒,虞舜安能复禅禹。焉得世人皆此俦,蛟龙尽入沧溟游。”(《骑龙行(并序)》);“涧水卷山木,势挟秋雨来。郁郁盘烈风,阴气凝不开。千崖争回旋,喧豗如奔雷。合流驱巨川,一气安可回。横冲蠮螉塞,直下燕王台。白波荡平土,蛟室何崔嵬。苍茫破寒坝,连空白皑皑。天心亦何极,念此生民哀。”(《北涧观水入桑乾时久雨泛滥阴失经也》);“霜下孤城幕府高,异乡消息梦魂劳。天涯兄弟悲秋雨,乱后江山入变骚。惨淡边声惊朔雁,苍凉野色上征袍。临关莫洒征夫泪,苏武终年拥节旄。”(《秋行役怀伯兄》);“空岩閟寒景,幽栖淡尘事。风掠黄楂林,月上寒山寺。所怀青松下,幽人抱琴至。”(《山寺月》);“高风落庭树,荆舍忽已秋。山路鸣寒蝉,清泉门外流。农人傍我行,送我归田畴。妇子出侯门,相见语未休。道衰亦已久,处世拙所谋。欲学餐霞人,长啸归林邱。”(《山居》);“疏林带寒雨,空山响秋叶。泛泛广川流,凄凄晚风入。山中岁云暮,深宵客愁集。繁星鑑方沼,露湛凉簟湿。赖兹端忧辰,喜与嘉宾接。”(《陈弢庵太傅入山来访》);“朝行西山麓,暮行西山麓。山行无远近,泉声断相续。”(《西山》);“登山望平川,关塞何悠远。孤城隐寥敻,苍茫亦在眼。白日行寒空,秋风下长坂。中原莽无极,俯仰志不展。欲谢行役人,回车今已晚。”(《秋日西山望》);“万象随秋气,微霜薄野亭。诗篇和泪尽,关塞入愁青。任昉门无客,灵均酒独醒。乘桴何日事,归去钓沧溟。”(《立秋》);“登兹览八极,日月光昭回。边风摇北辰,下拂云雷开。关山正相望,莽莽秋雨来。侧闻燕昭王,遗迹青山隈。蓟邱俯流水,霸业安在哉。千金聘骐骥,乐毅何能哀。日暮瞻回川,万里空黄埃。”(《登台》);“清光银汉月,永夜照空坛。乍叹秋云薄,翻知玉宇寒。高风催露下,孤客揽衣看。尊酒吾生事,林中强自欢。”(《七月十二日北坛见月》);“明月知时节,深秋照客衣。阶庭寒露下,江汉白云稀。报国心无改,乘槎梦已非。栖迟归独卧,幽意莫相违。”(《七月十四月》);“片云东南来,忽不见秋月。欲登蓬莱巅,青松恐衰歇。飒飒听流水,枕席生寒风。秋夜金井阑,飘落双梧桐。岩峦抱城郭,千山尽朝东。中有羽衣客,策杖撷紫茸。白猨不可上,飞鸟安能穷。我欲从之去,长天骑赤龙。”(《西山秋夜》)。按:《七月十四月》在天津图书馆藏“自书三卷本”中即作《七月十四月》,可能是“十四日”手书之误。
〔5〕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按:溥心畬之兄溥伟为小恭亲王,其妻丧于1933年,时《益世报》有《溥伟在连丧妻 溥儒鬻画隐居西山八年》的报道(见《益世报》1933年1月23日)。故诗中《蕴香斋遗诗》非心畬之嫂的诗集,而应是其嫂所读之书。有清一代,以蕴香斋作诗词集名的即有周徹、叶静宜、陈桂生等,本诗言及之《蕴香斋遗诗》具体为何人所著,尚待考。
〔6〕袁思亮《蘉庵文集》(卷四)“萃锦园介寿记”,袁荣法编《湘潭袁氏家集》(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302—204页。按:《湘潭袁氏家集》(二)无具体出版年,内文为手写誊印。现据《湘潭袁氏家集》(一)第158页按语纪年“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乙卯九月识于台北后野史亭”,推测该书出版于1975年。袁思亮(1879—1939),字伯夔,一字伯葵,号蘉庵,别署袁伯子,湖南长沙湘潭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试礼部未中后绝意于科举。民初曾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秘书、国务院秘书、印铸局局长、汉冶萍矿冶股东会董事等职。袁世凯复辟,弃官归,隐居上海,终日以著述、购书为事。所藏宋元古籍甚多,喜收诗文集。其父袁树勋,字海观,官至山东巡抚、两广总督,亦喜藏书,宣统元年(1909年)曾出力创办山东省图书馆。藏书处曰“雪松书屋”“刚伐邕斋”等,藏书印有“刚伐邕斋秘籍”“湘潭袁伯子藏书之印”“壶仌室珍藏印”等,著有《蘉庵文集》《蘉庵词集》《蘉庵诗集》等。
〔7〕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8〕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9〕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10〕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年(1871年)授编修,同治十三年(1874年)升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十一年(1885年),应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赴台,返闽后修葺先祖赐书楼,并建沧趣楼。自此闭门读书、赋诗。宣统元年(1909年)调京充礼学馆总裁,辛亥革命后仍为溥仪之师。1935年卒,谥号“文忠”。
〔11〕朱益藩(1861—1937),字艾卿,号定园,江西萍乡莲花人。光绪庚寅翰林,官至湖南正主考,陕西学政,上书房师傅,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辛亥革命后回籍。1916年受邀进故宫为上书房师傅,教授溥仪直至1924年。溥仪至津后,他管理“清室北京办事处”,仍为溥仪负责谋划。九一八事变后,朱益藩“主拒不主迎”。溥仪出关,他不但没随行,且至死未去长春。
〔12〕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言、叔韫,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后逃亡日本,参与了伪满建国活动。罗氏一生搜集并整理了大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13〕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1898年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1900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后因病于次年返国。此间,曾任教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有开拓之功,代表作如《红楼梦评论》《静庵诗稿》《人间词话》。辛亥后,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此后研究转向经史、小学,涉猎甲骨文字及商周史研究,相关成果汇编成为《观堂集林》。1923年春,经升允推荐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4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家人阻拦而未果。此后,经胡适、顾颉刚推荐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并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研究。1927年6月2日,在颐和园昆明湖沉湖自尽,得谥号忠悫。
〔14〕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15〕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16〕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17〕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卷八),文海出版社1972(民国六十一年)年版,第322页。按:颖生为高向瀛,与弢庵同出闽地,光绪十四年戊子科举人,曾与何梅生、刘龙生组“三生会”,结社唱和。
〔18〕耆龄《赐砚斋日记》“四月廿八日”,《中和月刊》1944年第六卷第1期,第574页。
〔19〕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1923年8月下旬)》,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页。按:短札涉数人,敝宗人为心畬岳父升允,因汉姓罗,故罗振玉称其为敝宗;颍川本是汉代陈蕃的字,此处为陈宝琛之代称。升允(1858—1931),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蒙古镶黄旗人。清廷授多罗特公,历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职。宣统元年,升允因上疏反对立宪,以妨碍新政之过失被革职,之后寓居西安。武昌起义爆发后,重新被启用,任山西巡抚总理陕西军事。升允率甘军东进,连下十余城,逼近西安。1912年2月,清帝溥仪退位,甘军得知消息后拒不作战,升允西退。此后往来于天津、大连、青岛,结纳宗社党人,谋划复辟事宜。1931年病逝于天津租界,溥仪赠谥曰文忠。另,札中楫先是陈宝琛同乡佟济煦,满洲镶黄旗人。少时中秀才,后就读福建全省高等学堂,毕业后在厦门官立中学堂任教。1909年到北京,任教于北京贵胄法政学堂(据《心畬学历自述》,溥心畬曾入贵胄法政学堂读书,当为楫先学生)。辛亥后,在北洋军政府总参谋部及北京南苑航空学校任职,主管技术引进等工作。因接触新技术,后从事照相及出版业,创建最早影印内府藏历代名人书画的出版社——延光室。1924年入紫禁城任职,协助郑孝胥整顿内务府。后随溥仪出故宫到天津,直至满洲国任宫内府近侍处长。
〔20〕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1923年8月下旬)》,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页。
〔21〕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22〕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
〔23〕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1923年12月15日)》,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99页。
〔24〕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1924年1月2日)》,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602—603页。
〔25〕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1924年1月中旬)》,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605页。
〔26〕庄士敦曾依《论语》“士志于道”一句起“志道”之号,与“明道”之意吻合。且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整顿内务府”一节记叙,庄士敦也正是力荐郑孝胥的人。
〔27〕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2016重印,第1978页。
〔28〕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2016重印,第1978页。
〔29〕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1983年第7次印刷,第161页。
〔30〕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1983年第7次印刷,第161页。
〔31〕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1983年第7次印刷,第157页。
〔32〕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1983年第7次印刷,第159页。
〔33〕该文原发《传记文学》第4卷第2期(1964年2月),收入《李宗侗文史论集》,本文所引为集中所收之文附录的《溥心畬致陈弢庵的信》。李宗侗《李宗侗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40页。
〔34〕李宗侗《李宗侗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40页。
〔35〕《西山集》卷三还录有《陈弢盦太傅招饮钓鱼台》一诗(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虽未注明时间,然其后有《癸亥秋七月西山怀海印上人》,且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卷八有辛酉钓鱼台宴诸旧之诗,故知此事当发生在1921年至1923年之间。此时,溥心畬亦有“弢盦”之称谓。且,另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中“散原精舍诗卷上(起光绪辛丑讫甲辰)”中即收录《实甫由闽中寄新刊诗卷次其卷中与陈弢庵阁学师唱酬韵即寄》一诗(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卷》,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亦知弢庵虽为陈宝琛晚年之号,然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就在遗民圈中广为使用。
〔36〕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03页。
〔37〕致陈宝琛信函中称“浃辰而归”,浃辰为“十二日”,与出游月余不符,似应溥心畬的虚数之称,非实际行程时间。另,该组诗以“秋”为意,与农历前后季节不合,亦应是表达“愁绪”的修辞需要。
〔38〕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1924年8月27日)》,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633页。
〔39〕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1924年8月30日)》,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634页。
〔40〕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41〕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42〕溥儒《西山集》(卷三),毛小庆点校《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43〕画作曾发表于詹前裕著述。詹前裕《(台湾近现代水墨画大系)溥心畬——复古的文人逸士》,艺术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杭春晓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