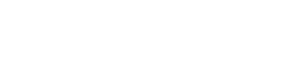在当代语境中,要想成为有文化的人,就必须抵制主流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可能被视为反文化。然而,这种追求仍然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我们的本性。修养是通过文化成长为一种独特的个性,是一种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总是寻求更全面的涵盖,是一种对生活的认识,是一种智慧。这种渴望指向一种绝对,一种人类既渴望又无法获得的全知:如果我信教,我可以称之为上帝,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称之为善。这种善是我们只能为之服务的东西……
下面,我们来谈谈我对这篇文章最感兴趣的地方。Tatol的《曼哈顿艺术评论》的评论引起了人们如此的注意,这确实很罕见。“负面批评”的这个概念热情洋溢地为其赋予了思想纲领——而这个纲领听起来就像是回到了不久前还被认为是致命的本质主义的东西。这种“准神学”的语言是否是一种挑衅,就像Tatol的那个“五星评分系统”一样?如果是的话,那这段话的含义就更令人迷惑了。
据我所知,Tatol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绝对的”审美标准被视为反对相对主义的堡垒,而审美相对主义则被认为是当今批评家对作品质量缺乏关注的根本原因:“如今,只要有人提出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好,尤其是在艺术领域,就会引起混乱和争议。”
Tatol关于艺术标准的理念必须高于任何具体艺术家有限的、人类的自我辩解,以防止出现“我只是喜欢我喜欢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他看来,这样的说法剥夺了我们追求更好的理由,让我们陷入平庸艺术的泥潭。一件艺术品并不是因为“你说它好”才好,而是应该追求更高的标准——不是“我觉得好”或“你觉得好”,而是“它真的好”。
这种对审美修辞转向的呼吁,似乎是对当代文化生活中自作聪明的商业主义和缺乏对知识的严肃态度的反应——这些都是非常真实但又令人沮丧的现象。既然“负面批评”不仅是个人喜好的代言,而且是一种可以效仿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就将展开解释。
 “好”的局限
“好”的局限
首先,Tatol的理论给我提出了几个难题。
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否定“罪恶的快感”才能欣赏到“严肃的艺术”。我理解提倡艺术需要高难度的必要性,但我认为“罪恶的快感”本身也并没有错。在人生的不同时刻,不同形式的文化会有不同的作用。为什么一定要在“我喜欢真人秀”和“我喜欢阿彼察邦的作品”中做出选择?
在我看来,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反映了该理论所针对的抽象层面
(我曾说过,人们认为的“文化愚钝”至少有一部分与人们工作过度有关——当你工作得非常非常累的时候,很难抽出时间来欣赏“高难度”的高雅文化)
。
其次,如果你承认品位是主观的、判断是相对的,那么从逻辑上讲,你是否就必须放弃所有论证“有些东西比其他东西好”的可能?我不这么认为。可以有多种标准、多种方法对事物进行评判。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比20世纪30年代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撰写《前卫与媚俗》(Avant Garde and Kitsch)时更多元化。后现代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某些部分只是对这一事实的承认。在这个层面上,审美多元化是件好事——尽管它为制定统一的评判标准带来了一些新困难。
第三,即使如Tatol所说,“准神学”美学标准的提法只是一种激励人心的理想,是一种对超越价值的向往,它使你摆脱了自视,但这似乎也是虚妄的。对“绝对标准”的定位只会让你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人,你是站在自己有限的、受社会条件制约的立场上看待艺术的,你个人所熟悉的“好艺术”会塑造你对“艺术质量”这个概念的理解。
对我来说,艺术的困难和乐趣就在于不断出现新的欣赏方式,新的群体如何发明出意想不到的新的品味形式,以挑战从前的标准。Tatol所选择的参考文献实际上就体现了这种动态:音乐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会认为摇滚乐是严肃美学的绝对禁忌,是艺术的死亡;而Robert Christgau则发展出了对摇滚乐超精细、超严格的评判方式。
 Herman Melville创作的《白鲸记》木刻版画插图,图片:Photo by Fototeca Gilardi/Getty Images
Herman Melville创作的《白鲸记》木刻版画插图,图片:Photo by Fototeca Gilardi/Getty Images
 白鲸与毛毛虫
白鲸与毛毛虫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无意中产生的错觉效果。在《负面批评》中,Tatol举了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笼统的“主观绝对主义”(即“我只喜欢我喜欢的东西”)会使我们无法对作品的质量做出更整体、更有影响的判断:“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主观上会倾向于喜欢《饥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而不是《白鲸记》(Moby-Dick),但一个二十岁的人应该能够辨别出,后者在客观上是一部更好的文学作品。”
 2017年11月23日的费城,“饥饿的毛毛虫”的气球出现在当地的感恩节游行上,图片:Photo by Gilbert Carrasquillo/Getty Images
2017年11月23日的费城,“饥饿的毛毛虫”的气球出现在当地的感恩节游行上,图片:Photo by Gilbert Carrasquillo/Getty Images
问题是,这是在进行循环论证——我们是在拿一本经典文学读物与一本根本没有试图做同样事情的书进行比较。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也完全相同:“任何一个二十岁的人都应该能够分辨出《饥饿的毛毛虫》比《白鲸记》更适合给幼儿阅读。”
儿童读物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它有自己的经典作品,有自己评判的标准,甚至有自己的评论专家。根据那些标准,《饥饿的毛毛虫》有精美的水彩插图、别出心裁的形式和迷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好作品。
主观价值问题并不会影响质量问题。但我们必须从一个前提开始:即对什么人来说是“更好的”?
Tatol写道:“大多数当代艺术写作都将阐释作为回避质量问题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艺术本身不好,阐释就不可能被认真对待。”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个表述颠倒过来:“如果回避了阐释的问题,就不可能认真对待关于质量的争论。”
 插画家艾瑞·卡尔(Eric Carle,《饥饿的毛毛虫》作者)在一场图书签售活动中,图片:Photo by Vince Compagnone/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插画家艾瑞·卡尔(Eric Carle,《饥饿的毛毛虫》作者)在一场图书签售活动中,图片:Photo by Vince Compagnone/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两种成熟模式
两种成熟模式
不过我在总体上仍然欣赏Tatol在《负面批评》中提出的使命,即批评的意义在于为成熟的艺术树立榜样。我想我对“成熟”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Tatol非常强调要重视难度和严肃性,要超越那种与孩童时代相关联的轻松、不成熟的乐趣。他认为,强烈的“负面批评”对批评对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是让你实现这种超越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知识上的“成熟”也是指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认识自己。也就是说,从简单地通过定义个人品味来塑造自己的身份感,转变为对别人为什么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感到好奇,并有意识地让自己与这些品味进行对话。这是一种积极的协商——我不想只是被动地接受别人告诉我的好东西,我也不想只是武断地把自己对好东西的理解强加给别人。在这里,我想引用知名艺术评论家Peter Schjeldahl曾经就判断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写过的一段话,这与Tatol的观点形成了很好的对照。前者将自己作为评论家的职业经验总结为124个字:
我保留自己的个人品味,以处理我所看到的各种艺术作品。我有一个诀窍,可以让不讨我喜欢的作品也得到公正的对待:“如果我喜欢它,我会喜欢什么呢?我可能会喜欢,也可能不喜欢。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会想:喜欢这幅画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人类学者。
我评估艺术的标准是质量和意义。后者对我的选题最具决定性,因为我是记者。有些我喜欢的艺术我不会写,因为我无法确定它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否也这么重要。这(些喜好)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如果没有它们,我作为评论家的思路就会枯萎,但这却又并不一定在我的评论任务范围之内。
 反动派与后现代主义者
反动派与后现代主义者
这篇文章可能太长了,但我希望它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努力践行我所宣扬的观点,试图公正地对待Tatol的论点,解释它的利害关系,并确定我与它的认知不同之处。但归根结底,他的“批评家之角”确实很有趣,活跃了业内的气氛,不管人们不同意那些短评,至少我们都还在谈论画廊的展览。
然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一场更大的讨论,是因为Tatol的“负面批评”理论是在传达一种挫折感,而这种挫折感反映了一个更大的东西。Anastasia Berg在《曼哈顿艺术评论》同一期的导言中写道:“批评的潮流再次转向。现在有很多批评家都在谈论‘标准’‘质量’和‘美’等等,而且不仅仅是那些老顽固们。”
我认为这种强调部分源于一种感觉——Tatol直接而精辟地阐明了这一点——即超级消费主义不断塞给我们审美低劣的产物,还让我们认为它们的存在是合理的,许多领域(电影、音乐、文学以及艺术)的文化生态系统都正在接近一个严重熵增的点。千禧一代面临的社会进步渠道越来越窄、越来越残酷、越来越难以接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反弹,因为许多对人意义深远的经典艺术,在近些年来都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受到了混乱和还原性的批判,以至于现在有不少人都将“社会公正”视为了反智主义的同义词。
危险的是,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挫折感都可能被引向不同的方向,各种意识形态的精英们都希望利用这些挫折感。
在《负面批评》中,Tatol写道:
学会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好”与“貌似挺好”,什么是“尝试向好却失败”与“不可救药的坏”,这个过程是没有规则可循的,它不像公式那样可以被学习。在一个文化机构普遍衰落的社会里,许多人甚至没思考过这些东西,更不知道让自己接受和了解这些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文化和自身的利益,判断好与坏,真实与虚假、深刻与肤浅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就变得加倍重要。
这话听起来与Jordan Peterson——一位广受欢迎但有点古怪的新荣格派哲学家——的观点很像,他在谈到后现代主义者的罪恶时说,他们给艺术带来了“对区分质量的憎恨”:
在健康的文化中,艺术家的作用是让公众认识到尚未进入他们意识的存在要素……艺术家推动我们向未知领域迈进……事物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质的区别”……你可以登上真正的高度,这意味着它们高于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有这些东西可以追求,就赋予了你生命深刻的意义和重要性,赋予了你奋斗的崇高性和有效性。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质的区别”的绝对敌人,他们所做的就是摧毁每个人的雄心壮志。
而Tatol在哲学方面主要的参考文献源自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他们都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但不是“质的区别”的绝对敌人)
。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同意Peterson的保守主义政治世界观。但请注意,我并不是把Sean Tatol的批评理论与Jordan Peterson的大师之见相提并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人与艺术的联系可以改变生活,是我们所向往的,这种观点无可非议。
 2018年11月2日,Jordan Peterson在剑桥联合会,图片:Photo by Chris Williamson/Getty Images
2018年11月2日,Jordan Peterson在剑桥联合会,图片:Photo by Chris Williamson/Getty Images
Peterson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西方文化”和“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如何受到“恶魔般”的女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然而,在《负面批评》一文中,Tatol只是粗略地试图把自己的观点与周围“反觉醒”的虚张声势区分开来。
(虽然我也认为《尤利西斯》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经院哲学代表人物)很伟大——但Tatol提供的所有文化“成熟”的例子还是来源于传统的西方典范。)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或许是将审美多元化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予以审视——说它并不总是知识懒怠化的代名词,也可以是好奇心的代名词;它不是拥有标准的障碍,而可以是理想的起点。我不禁要问,在某种程度上,呼吁将艺术批评根植于对超越所有语境的“绝对价值”的取向,是否会成为一种方式,以避免在我们在纷争不断的当代语境中,对这一呼吁所产生的更不幸的共鸣进行反思。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
 “好”的局限
“好”的局限 Herman Melville创作的《白鲸记》木刻版画插图,图片:Photo by Fototeca Gilardi/Getty Images
Herman Melville创作的《白鲸记》木刻版画插图,图片:Photo by Fototeca Gilardi/Getty Images
 白鲸与毛毛虫
白鲸与毛毛虫 2017年11月23日的费城,“饥饿的毛毛虫”的气球出现在当地的感恩节游行上,图片:Photo by Gilbert Carrasquillo/Getty Images
2017年11月23日的费城,“饥饿的毛毛虫”的气球出现在当地的感恩节游行上,图片:Photo by Gilbert Carrasquillo/Getty Images 插画家艾瑞·卡尔(Eric Carle,《饥饿的毛毛虫》作者)在一场图书签售活动中,图片:Photo by Vince Compagnone/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插画家艾瑞·卡尔(Eric Carle,《饥饿的毛毛虫》作者)在一场图书签售活动中,图片:Photo by Vince Compagnone/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两种成熟模式
两种成熟模式 反动派与后现代主义者
反动派与后现代主义者 2018年11月2日,Jordan Peterson在剑桥联合会,图片:Photo by Chris Williamson/Getty Images
2018年11月2日,Jordan Peterson在剑桥联合会,图片:Photo by Chris Williamson/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