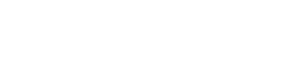兼具画家、鉴藏家、史论家等多重身份的黄宾虹是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派代表人物,亦是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先驱。他在1923年至1924年间发表的《中国画史馨香录》中系统总结了自己早年间对美术史的研究。尽管因故未能完稿,但其通过以画家传记缀连美术史的叙述体例以及实证汇编、论融于史的写作手法,诠释了对中国美术的总体认识。20世纪初,在中国传统画学向现代美术史学转型的学术语境下,黄宾虹从传统绘画的本体规律出发进行学理建构,通过对传统文脉的深度发掘与活态运用,确立了与当时诸家多有不同的美术史研究模式。
1925年,《古画微》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之前,该书作者黄宾虹对传统中国画学、画史进行了独立、具体且深入的研究。1907年至1913年间,黄宾虹陆续发表了《梅花古衲传》《江允凝传》等研究中国古代画家、画派的文章,还与邓实合编了《美术丛书》。除上述著作外,早于《古画微》发表的《中国画史馨香录》(以下简称《史录》)似乎很少为学界所关注。事实上,这本于1923年7月25日至1924年8月12日分期连载于《国民日报》副刊《国学周刊》上的著作是黄宾虹首次尝试撰写中国画通史。在本书中,他以画家传记的形式串联起了中国画璀璨的发展历程,他遵循中国画的递变规律和内向探寻的学理思路,找到了一条“纯正”的绘画史叙事脉络。

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的《古画微》书影
1923年7月,黄宾虹开始在《国学周报》上连载《史录》。从《史录》开篇即可看出,黄宾虹的写作动机在于“综先哲之旧闻,阐艺林之奥旨”,即从纷繁芜杂的文献典籍中梳理出最具代表性的画学主脉与文化典型,祛除其中消极、陈腐的因素,用以“鼓舞后学,发扬天机”。撰写《史录》时,黄宾虹并没有采取类似于陈师曾、潘天寿、郑昶等人在画史写作中运用的历史分期手法,而是有意弱化中国画发展中的“阶段”概念。这与当时许多传统派美术家的理念有着很大不同。比如,郑昶把绘画的演进分为“漫涂”“形似”“工巧”“神化”四个阶段,建立起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逻辑,且把美术史按照时代划分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
这些以“阶段”“进程”为索引的叙史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是一种引西润中的文化策略。虽然这一策略与反传统的一些美术家所沿用的逻辑话语在本质上是相近的,即由西方美术的演进过程推导出“公例”,再与中国美术史进行比较,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机械地尊崇所谓的“公例”,而前者是既在东西方文化中寻找差异,同时又探索共性,最终建构起中国美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黄宾虹 《山城郁秀》 75.4cm×31.7cm 纸本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黄宾虹虽然身处传统阵营,但《史录》的叙史手法既带有一定的线性思维色彩,又刻意模糊发展“阶段”,着意弱化美术史中的分期概念。就像黄宾虹在绘画上反对盲目的中西融合一般,他认为西方绘画的发展自有其社会土壤与文化语境,中国画的演进亦无法脱离开自身的民族环境来看。
他于1918年在《时报》上刊出的《附增美术周刊预告》一文中写道:“第今日之谈美术者,醉心欧化,尤当保重国华。如建筑然,先有基础,而后丹垩涂泽可施于宫墙。如树木然,先有根柢,而后华叶果实得敷于枝干。”这段话的意思是,美术史的书写应当“保重国华”,同时要从搜集、考证、梳理文献史料入手,因为“绘事常因文化为转移,名家即由时世而特起”,而非急于给绘画史定性,或“预设”绘画发展的方向。或许正是这种审慎、理性的心态以及注重叙史过程的方法论,促使他选择了以画家入手讲述美术史,从而促使其形成了注重文献实证的内在学理路线。

1923年《国学周刊》第12期发表的《中国画史馨香录(一)》
搜集、梳理、汇编画家生平与画论文献是支撑黄宾虹撰写《史录》的核心要素,因而注重实证是《史录》最为直观的特点。在“两汉士大夫画”这一章节中,黄宾虹通过引述《汉书》《后汉书》《元丰类稿》等诸多史料文献来说明汉代绘画的功能性和艺术性,几乎做到了“有论必有史”的程度。由于两汉年代久远,黄宾虹十分强调要通过画像石来分析当时的绘画面貌,认为“今可见者,后汉石刻画而已”。他以东汉的石刻《李翕西峡颂》为例,提及“《李翕西峡颂》称翕尝令渑池,治崤嵚之道,有黄龙、白鹿之瑞,其后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连理木之祥,皆图画其像,刻石在侧”,说明画像石对当时的社会事件具有记录功能。
黄宾虹不是机械地汇编和总结文献,而是在搜集大量与论题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有所修改和整合,因而,《史录》能保证内在的连续性和逻辑的通顺,最终使这些文献为自己所书写的美术史服务。可见,黄宾虹的相关做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亦有借古开今之功。

黄宾虹 《汉阳归舟》 73.8cm×32cm 纸本设色 1954年 中国美术馆藏
中国传统画学写作不会刻意区分“史”与“论”。黄宾虹在写作《史录》时,亦运用了论融于史的手法,为的是勾勒出完整、饱满的画家生平及其所处时代的整体艺术风貌。例如,概述顾恺之时,黄宾虹先将文献史料中对顾氏的记载梳理成文,记述其生平故事与绘画造诣,后从《历代名画记》中摘录其画论,同时指出其中的舛谬之言,认为学者应该“掇其菁英,弃其糟粕,不以词害意焉可矣”。

1925年《东方杂志》第22卷第3期发表的《鉴古名画论略》
黄宾虹的《史录》还在实证汇编、论融于史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评述,其中有两个特点最为明显。一是对中国画发展之延续性的高度重视,即对取法、流变与传承关系的厘清。他在论述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时言及“李氏父子笔墨之源,皆出于展子虔辈”,认为荆浩的山水“承吴道子、王维一派,而不为其范围所囿,故其笔墨特高”且“为范宽辈之祖”,此外还提到了“然得董源之正传者,巨然为最”等,这充分说明他对中国画笔墨与艺术精神的传承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能活化运用。二是对画家天资、学养、人品等要素的强调——这是黄宾虹衡量画家的核心标准,也是其评论画史的重要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画学多以“文人画”“士夫画”为正统,学人亦常将此类画作区别于画工所作之画。黄宾虹则有意弱化画家的身份,以画家的学识修养替代这一标准。
黄宾虹能够跳出中国传统画学和诸多传统派美术家以文人画为正统的语境藩篱,在向内审视中国画本体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史料钩沉和艺术理念的输出,使得美术史论及其文化外延得以扩展,甚至对古人的画论有所匡正,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当下的美术史研究来说,仍具有借鉴意义。

黄宾虹 《湖山泛舟图轴》 96cm×42cm 1952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与陈师曾、潘天寿、滕固、郑昶、姜丹书等学者的美术史写作相比,黄宾虹受西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较少,其理论也与实用的美术教育关联较小。他依托于传统绘画的本体规律,以一种“内行”和“内观”的视角,用自己擅长的考据、鉴定、汇编等手法,梳理、整合丰富的文献、史料,阐发了自身对传统中国画的深层理解,构建起整体而延续的绘画史发展脉络。

1934年《文华》第46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黄宾虹虽然在绘画史写作中痴迷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因循守旧或排斥新学。相反,他对传统的尊重代表了其内核是要从传统画学中汲取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资源。他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之上,探索出了独具个人风格的写作体例,对传统绘画史笼统浮泛、缺乏严谨性和系统性的弊病进行了改进。
黄宾虹并不反对革新,这从他早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举动便能看出。他反对的是一味西化、革除传统式的求新。他对传统绘画的研究是从文化内核出发且不断向外延展的,就像他在《史录》中对古代传统文化的评述:“古人文辞笔墨,无不寓意劝诫之思,画事虽微,皆关庭诏,技进乎道,恒与圣贤之心若互相符合,安得以艺事忽之哉!”也正是这种“技进乎道”的观念与对“圣贤之心”的追求,使得黄宾虹在进行美术史研究时不仅具备坚守传统文脉的理性与自觉,又具备应对时代发展与变革的洞察力。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