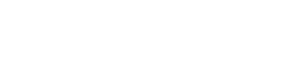摘要:在当前的深度媒介化社会语境中,媒介早以不同形式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而设计作为技术的最终呈现也属于媒介的一种,从媒介对象物、信息筛选、价值创造、媒介系统等媒介实践之中,设计师的角色也从最初的形式赋予者、信息设计者转变为媒介系统的创建者。
关键词:设计师;媒介实践;设计思维;设计与媒介
一、引言
“媒介”这一术语极具含混性和包容性,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一切“物”。据《韦氏大学词典》的释义:其一,通讯、信息、娱乐的渠道或系统;其二,艺术表达的物质或技术手段。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则认为媒介可以作为符号现象、作为物质/技术或者作为文化实践;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则将实践理论引入媒介研究领域,称之为“媒介实践”,主要集中对实践的社会性、行为的规律性、人的需求性、媒介行为的相关性进行考量。该文所讨论的媒介是以传播学为导向的“物质性”“中介性”为切角,从人与媒介的主客体间性的关系思考,将媒介视作对象物及介质物来阐释,也即一种新的存在论视角。
国际设计组织对设计最新的定义“设计旨在引导创新、促发商业成功及提供更好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将策略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应用于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的设计活动”①。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类比来看,设计自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也可理解为设计作为技术的最终呈现也属于媒介的一种,是设计与媒介物乃至多重物质间的考量。智媒时代,设计多样性与设计边界的不断突破,媒介的发展演变与设计同频共振在媒介对象物、信息筛选、价值创造、媒介系统等媒介实践之中,设计师的角色也从传统向创新路径发展。
二、设计编码赋形媒介对象物
设计师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将概念转化为有形的现实。从媒介的发展中回观,设计依附于媒介,设计师通过自身的隐性知识与编码功能赋形于各媒介对象物。设计在早期技术发展的语境中,其定位便是以自身设计能力作为手段提供竞争力,提供功能、形式及审美的解决方案,将可能的技术转化为具体的形式,无论是语言、视觉、听觉的符号现象,还是技术进路中的媒介重组的文化实践模式,皆在动态的进化过程中塑造着媒介形态。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肯定了媒介的广泛性与强连接性。口语是人类传播史中最原始的传播方式,至今仍然使用频繁,其为人际交流的传播符号之一,对于信息的编码也只在大脑内部进行,不需要外化为其他符号,进而产生的即时性是其他媒介所不能比拟的。当然,这里并不是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的讨论,而是遵循基特勒的观点来分析将口语作为“物质性”文化的可能性。
传播媒介的发展具有延续性,逐渐从听觉世界转至视觉世界。在历史的发展和传播延展过程中,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来突破口语传播中时间与空间场域的限制,从而创造出各种传播方式与媒介形态。无论是以早期楔形文字为代表,又或是借助于介质来对信息进行外化、物化或是固化,如竹简、缣帛、纸张等媒介载体,都达到了传递信息的目的。这些媒介隐喻着独特的文化属性,承载的能指与所指往往具有时间与空间的特质,正如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对“时间型媒介”维度的界定。
视觉媒介日渐丰富,当前已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从以媒介技术进路下的中国古代邸报、民间小报的出现,到近现代的纸质媒介形态,开启了大范围、规模化、日常化的平面传播时代,其公告性是消息传达之方法的“外观原质”。作为最直观的尺寸、材质、油墨、字体、字号、图片或是编排的空白或线条等形式集合的版面,都是手握、目视、嗅寻的“物”,皆来自于设计对“版面功能”美感及信息公布的呈现。莫尔斯电报的发明拉开了电信时代的序幕,其中广播和电视的出现作为现代媒介链条上的重要节点,迅速地与大众建立起一种稳定而又牢固的传播关系。各类电子设备、互联网、数字媒体、应用软件等跨媒介属性呈现出视听一致的景观式生产,而此时的设计师已不再囿于视觉图像的制造,而是朝着系统性的、战略性的创造方向发展。
在早期经验的触及与表达物质性媒介阶段,设计产出往往是生产者与设计师为同一人。至1919年始,设计师开始转向职业化,媒介载体也从文本向超文本演进,设计既涉及互动性叙事的变化,又涉及媒介接触的连续性。将设计作用于媒介对象物,在传播中以具体形制进行,也是作为设计话语实践的媒介和传播②。设计师对具体的媒介对象物的形式与美学塑造的角色主导,所体现的设计价值观既是媒介的实践也是文化的实践。
三、以设计作为创新手段的信息设计者
设计从依托硬件产品为主的物质形式转向以数据计算为主的信息、景观式的数字生产形式。在产销者为一体、双向性去中心化交流模式为主导的时代,新媒介主要突出表现为功能上的更替、组合、升级,并以叠加的方式向前发展,媒介传播的信息与设计方式也呈动态的创造性破坏模式。媒介赋予设计的信息传导进而显示出由单一到多元、由静态到动态、从实体到虚拟、从单维度到多维度的趋势。设计的产出注重组合相关要素,加强与技术的密切对话,已逐步从附属于产品的阐释者、说明者扩展到创新产品线战略的区分者,设计师通过信息分发、流量池、元数据、存档等相关要素的模态组合转译,以此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观。在媒介多重性程序背后,更深层次的是信息分发模式和设计方案的生成,从媒介传播形态由“线”到“网”到“云”的变化中,“传输”到“连接”到“生成”成为媒介实践的主要行动逻辑③。
设计/技术作为手段的媒介延伸。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门户网站的陆续建立,信息渠道也从电脑端拓展到移动端,人的主体性已偏于向节点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共同参与到信息的分配、分享及实时讨论中。时刻在线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状态,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消解了传统媒体作为主体的唯一性、专业性和单向传授关系,同时也被搜索引擎编入索引,使受众的解释行为得以多向度延伸。此时,数字技术扮演的角色是“允许所有信息,包括声音与影像,都可以采用封包方式传输,形成一个不需要控制中心就可以在所有节点相互沟通的网络”④。设计同媒介一样具有居间作用,物/技术的媒介化也秉承着媒介信息的承载性,尤其在穿戴式设备、芯片植入、人工智能等媒介实践中,设计与媒介的中介性将人体自身演变为信息集成的“本媒体”⑤。这与麦克卢汉所提到的媒介是人类的进化式延伸理论相照鉴,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认为媒介的发展将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方式朝着人性化趋势演进,但在当前的这场媒介实践中,正是如同安德里亚斯·赫普(Andreas Hepp)所说“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表现。当然,需警惕被“延伸”闭塞,这对于设计伦理及其媒介素养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集聚的信息流以及视频流,正在合力构建不同于文字时代、图像时代的数字文化景观,打破了“生产—文本—受众”的线性流程架构等实践模式。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75亿⑥,这组数据表明物质生产结构已转向影像、视频化为主导的景观式信息生产,在居伊·德波(Guy Debord)看来,景观的出现是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⑦。平台和用户是实践中的主体,也是协同设计的有效方式,二进制平台主要表现为算法管理、内容生产、编制协议等,实现流量最大化等设计行为,而用户的媒介实践则表现为参与文化和交往实践的设计行为。在此,平台与用户被赋予了设计师的身份,进行着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处于共存的社会化媒介实践,在媒介消费、媒介经营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时候,渐渐转化为深度媒介化阶段的设计行为⑧。但由于各平台分发模式、用户的源信息差异不对等因素,需要警惕设计、劳动及信息的去物质化所造成的社会负面效应。
设计师基于对信息模型的设计、美学参数的创建、数字媒介的编码等重组优先信息,并不仅在于对信息的传达,而是在复杂系统里创建能承载这些信息的空间、有效信息的整合与筛取的创新方式。此时,媒介赋权下的设计师在媒介话语建构中,对社会信息的形塑采用新的循证方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来保持设计系统观的媒介化生存,维持媒介信息生态平衡。
四、自我增值与价值创造的整合者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述的第三媒介时代,为适应社会语境与技术语境的变化,设计师自我增值的必要性突出。其不仅作为设计策略和设计流程的管理者、信息与传播过程的设计者,亦是未来媒介生活方式的创造者,成为社会信息的整合者。密切把握与各方的协同机制,参与媒介实践场域的探索,以非正式自发性的方式拓宽思维和技能,与新媒介/新技术一起共同进化。设计师在自身媒介化的同时需不断地以媒介化方式思考,不断地在未来新发展背景下思考如何精准有序地推进设计对社会信息价值、文化价值的创造,以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世的设计。
整合同创新、媒介、商业、研究及消费等可持续发展资源的能力,共同进行创造性活动。约翰·赫斯克特(John Heskett)曾提到,在设计史研究中整合生产与消费领域是裨益颇丰的事情,从现实来看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就学科分类层面而言,媒介理论作为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前沿,因此研究也较多集中在传播学领域,而与设计学科的交叉融合鲜少涉及,在当下的数字媒介实践中,信息传播的方式对设计师来说无疑是对设计工作范畴和流程的整合。借鉴其相关新的设计方法和研究工具,设计师需要具备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设计能力,来处理广泛的信息和媒介程序,以满足复杂系统的需求。
同媒介产消者的协同价值创造。数字媒介背景下无需构建整体的生产线,柔性制造满足以个人需求为导向的生产,从“为人设计”转变到“与人一起设计”积极囊括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设计过程。通过与设计对象的交互,提高个体在参与设计过程中的能动性,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多主体性、协同性、共同性及灵活性等方面,设计师的角色也从强调创造最终形式的设计者转变为创建出最能让用户做出重要决定的推动者,在未来设计领域的人工智能辅助设计上将会成为新常态。设计作为一种探索媒介,无论是参与过程形式的协同设计,还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商讨式设计,设计协作对于设计师来说都是长期的过程状态,设计师则以一种产销者的模态存在于媒介实践过程中。
设计特质的共同体需保持对媒介素养的提升。媒介素养一词由英国学者利维斯(FR Leavis)等人提出,强调对各媒介的使用能力和信息的解读及批判能力。为确保设计信息的有效传达,融合各媒介平台的设计机制、深入洞悉用户主体的媒介惯习、数字交互方式的场景创新等媒介生成,是设计师及设计共同体的基本媒介素养。对媒介的隐喻性、媒介的行动力及媒介逻辑的连续性研判,将“物性”生发为意义空间,也是设计师的价值与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在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看来,设计除了作为商业价值的实操者之外,也可以作为批评的媒介。全面反思技术、文化、社会与伦理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力,亦是说设计作为批评媒介的活性维度是比较有弹性和张力的。数字媒介实践中的路径将铺设更广泛的面向,如:使用媒介的行为和以媒介为前提的行为的设计;随时保持接触的需要、信息的需要、维持公域在场的需要等。这些都是围绕媒介的变革来进行衍生的相关设计方法,设计师以此进行的节点化信息设计、媒介惯习的设计等皆可作为批评和观照的媒介。
五、差异化赋能媒介系统的创造者
建构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之上的全新社会形态,设计也早已从对媒介对象物的造型转变至对媒介物的链接,进入了一个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沉浸式媒介系统⑨。设计师对媒介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作用力凸显,以点带面的设计系统思维能够有效地拓展,多场景、多并发、多类型终端、全时在线的信息互联状态,正是设计师通过高度语境化的不同中介方式而具体化的模塑力⑩。延至技术语境下为主导的媒介服务带动的场景塑造,设计师作为战略家的角色,赋能社会创新设计,从而为媒介生态系统动态关系而设计。
以技术为主导的媒介系统设计。在媒介技术拥趸下的如VR、AR、MR及VR+等各类沉浸技术而产生的信息形态,个体穿梭于信息网络和物理空间建立的自身数字化生存状态,这种虚拟的媒介观,或许就是意义汇集的空间⑪。从历史背景的观照来看,媒介、设计同技术一道呈组合进化的趋势,数据成为万物互联的流通介质,媒介产品的个性化与媒介终端的遍在性,使智能算法逻辑随媒介系统深入生活的各个维度。个体“人”也成为了复杂的行为媒介主体,其思维同时也成为媒介系统设计与更迭的根本立足点,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动态系统的途径,思考媒介的变量和标量,每一媒介系统都是设计师用于转码的机器。
以场景塑造为主的智能化信息生态系统。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曾用“媒介生态”一词来表示过程与客体存在于事物模式与物质的大量的动态关系。设计伴随场景塑造的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模态,也不断地在场景的坍塌和重建过程中进行具形互动。个体媒介行为与数字接口的交互为智能可穿戴设备的连接与感知、无接触送餐服务、智慧链接等塑造智能场景。以自动驾驶为例,按照人的视觉生物感知建模,此时,人、机器及环境各媒介系统因汇聚交织而运转的属性为:无机物的有机化,有机物的数据化。近年来,元宇宙的热潮仍在持续扩散,将催化全新的内容,其中,算力、引擎、数字孪生是重点突破方向⑫。也有学者认为元宇宙作为数字时代众多媒介技术发展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深度媒介化的实践⑬。
媒介的生长性不断地将先前的经验颠覆和重置,建立多维度的数字感知体系。媒介基础设施自身的运行逻辑,适时地调试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协作,同时也会隐性地促发引导设计师差异化设计相关属性,以供媒介系统的自然运行。设计师自身媒介信息的承载性,包括具备设计特质的共同体,也是媒介涵化主体的表征之一。技术媒介的运用与开发,重构了人与技术媒介的关系,但需警惕媒介技术侵蚀人的主体性,虽然设计师掌握着程序等手段的实施与更新,但技术却能够实现自治、独立、不为外部法则或者力量所支配。
最终我们热衷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及其即将展开的媒介实践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设计促发媒介作为技术机器系统,与有机系统、社会系统互嵌共生,成为驱动人类社会的动力和机制,其中诸种元素的转换与结合生长出创造性的生态媒介系统。多向传播方式与万物互联,更多的是一种数据与计算行为,在分析、决策、判断的设计行为中,设计开始从因果关系思维、关联关系思维到数据化思维的转换,设计师所具有的战略性的决策分析与部署,在接下来的媒介实践中将接受着考量。
六、结语
在传播学建制中的导向,媒介的物质性被功能主义的工具性长久地隐蔽,但数智化颠覆了传统媒体的技术逻辑,从而关注到以“中介性”为导向的媒介。媒介作为中介的探针,为设计研究提供手段并在媒介语境中解决问题。设计师对媒介的介质赋形与赋能,阐释了设计与媒介同步进化的趋势。赫斯克特提出的设计师角色变化模型体现在不同层次的设计实践中,那么在媒介循环进化的过程中,设计师的角色也有序地分布在媒介实践中,并从最初的形式赋予者转变到媒介系统的创建者。
当然,随着未来技术的发展还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以我们当下的想象力或许不足以做出准确深入的考证,需得以挑战及开放的心态迎接。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英才计划项目“媒介场景构建与协同设计研究”(编号:2021YC028)学术成果。
注释:
①Industrial Design Definition History[EB/OL].https://wdo.org/about/definition/industrial-design-definition-history/.
②Richard Ek,Falkheimer,Jesper & Jansson,André(eds.):Media Studies,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and Relational Space,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M].Göteborg:Nordicom,2006:45-66.
③姜红,鲁曼.“线传输”“网连接”“云生成”——数字化进程中媒介形态与实践逻辑的流变[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3).
④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M].刘君,周竞男,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54.
⑤段鹏,李芊芊.叙事·主体·空间虚拟现实技术下沉浸媒介传播机制与效果探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
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2-2-25)[2022-5-1]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202/t20220225_71727.htm.
⑦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4.
⑧Andreas Hepp.Deep Mediatization[M].London & NewYork:Routledge,2020:5.
⑨李沁.媒介化生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22.
⑩HeppA.Mediatization and the“molding force”of the media[J].Communications,2012,37(2):1-28.
⑪胡翼青.显现的实体抑或意义的空间:反思传播学的媒介观[J].国际新闻界,2018(2).
⑫北大汇丰商学院,安信证券.元宇宙行业201页深度研究报告:元宇宙2022,蓄积的力量[EB/OL].(2022-1-28)[2022-4-20]未来智库,https://mp.weixin.qq.com/s/X2vWXvHmhBxrOcSlwZV9jg.
⑬陈昌凤.元宇宙:深度媒介化的实践[J].现代出版,2022(2):19-30.
参考文献:
[1]玛丽-劳尔·瑞安.故事的变身[M].张新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6-24.
[2]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38-40.
[3]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6.
[4]黄旦,周奇,主编.媒介史的研究与书写[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5.
[5]克莱夫·迪诺特.约翰·赫斯科特读本:设计、历史、经济学[M].吴中浩,译.南京: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59-60.
[6]时迪.协同设计中的沟通方法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7.
[7]马修·福勒.媒介生态学[M].麦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4-7.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