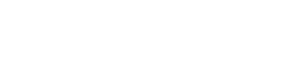明代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产品“专供御用”,其烧造活动不仅贯穿有明一代,御窑制度也为清代所沿袭。明、清两代数百年间,景德镇一直是御用瓷器的生产地。由于御用瓷器的供应对象是皇帝后妃等,而使用场所是皇宫,故产品输京成为御窑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御窑产品是如何按时、保质呈送到皇帝面前的?以往相关的研究不多。根据《江西省大志》“陶书”记载:“查往陶厂皆自水运达京,由陆运者,中官裁革后始也。”说明明代晚期御窑瓷器输京方式由水运改为陆运。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以丰富和拓展御窑考古研究的视角,并就教于方家。
一 御窑产品运输方式变革的内容
以往关于明代景德镇御瓷运输进京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前引《江西省大志》“陶书”部分“解运”条的记载:“查往陶厂皆自水运达京,由陆运者,中官裁革后始也。”这不仅表明御瓷输京存在水、陆两种方式,而且可知,“陶厂”(明代御器厂)的产品在嘉靖之前皆从水路进京,而陆运始于嘉靖朝“中官裁革”事件之后。“中官裁革”指的是朝廷废止了“宦官榷陶”的制度,时间在嘉靖九年(1530),《江西省大志》载:“管厂官自正德至嘉靖初,中官一员专督。九年,奉文裁革,于各府佐轮选一员管理。”所以,御瓷运输采用陆运始于嘉靖九年,这是明代御窑瓷器生产与运输管理制度上的一件大事。至于陆运的线路,据史料记述认定为从景德镇北行,到浮梁,再北行至池州交接,之后再由船运入京。陆运阶段的承运人役有抬夫、挑夫两种,表明以抬、挑为主。可见明代晚期改革后所谓陆运的实际行程只局限在景德镇到池州一段。这种说法和其他文献屡次提到的 “陆运”的线路并不全部重合,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说明。
有关改革以前御窑瓷器水运抵京,文献记载较多。水运线路大致如下:在景德镇昌江东岸装船〔图一〕,沿昌江入鄱阳湖,入长江,再入运河,由运河直抵北京。但截止目前中国内河的水下考古工作并未发现过明代御瓷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御用器物的生产、运输、使用等均有严格要求,发生意外的概率本身就比较小,即使损坏、散落也会尽可能的回收。反之,同样是以水运为主的民窑器,倒是时常发现于各处港口、沉船等遗存。而且民窑瓷器依靠水运的情况也见于大量的明代文献,说明这是当时的常态。通州张家湾出土大量民窑瓷器残片,一方面表明瓷器运输过程中损毁量之巨大,另一方面也证明沿运河北上是重要且习见的运输方式。传教士利玛窦也在札记中提到:“最细的瓷器是用江西所产黏土制成,人们把它们用船不仅运到中国各地而且还运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透过对明代驿传的研究,得知当时的“驿传交通,既有陆运,又有水运⋯⋯使用何种运输取决于运送的人、装运的货和目的地,或者是否时间紧迫而不计费用等因素。最快的运输形式是马运,但这仅适用于个人旅行或传送文书⋯⋯水运是运输大批人员和货物的最经济的方式”。数量巨大的御瓷,水运最符合当时的运输方式。明代法制规定各地所烧城砖的运输,亦均由运粮船带运入京。这或许可以作为水运官用物资的入京证据之一。

〔图一〕 清代青花御窑厂图圆瓷板
南方物资经运河水运至北京,于明代大部分时间一直畅通无阻,也是明朝政府得以运行的最重要的经济保障。从逻辑上分析,在水运可以直达的情况下,大宗的御窑瓷器舍弃水运改为陆运,并不符合常理。那么,嘉靖九年的这次调整是为了什么?改革后的陆运线路又是如何?究竟是昙花一现的偶然,还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据陆万垓《江西省大志》记载,“本厂见奉烧造瓷器,一年完解两运⋯⋯自嘉靖年间以来,俱由陆路进京”,可知从嘉靖九年改革到万历二十五年,御窑瓷器输京为陆运,采用“一年完解两运”的方式。万历时的工部典籍《水部备考》〔图二〕记载道:“上用供用磁器如遇缺乏,该内承运库传奉圣旨:钦降式样花样备行到部覆奉;钦依差人赍行江西饶州府,并行该省抚按布政司如数烧造,定限解进,大约每年二运,以五月、十月到部。承行该吏謄写清本送内承运库交收。原箱原封俱不启动。”御瓷每年运抵北京的常规时间为五月和十月。但再查隆庆五年的相关记载,可知每年“两运外之”还有其他批次,明确提到完成运输的时间有隆庆五年九月、十二月和隆庆六年二月这三个时间点,尤其是十二月和来年二月,是北方的冰封期,这是经运河水运入京时不得不考虑的难点,那么在运输的最后路段如何完成?需要研究。

〔图二〕 《水部备考》
根据《明神宗实录》中督陶官潘相在万历三十年(1602)提议建造十三条大船专运御瓷、三十四年(1606)又奏请改船运、三十五年(1607)再次奏请造船的记载,说明潘曾屡次努力以船运御窑瓷器入京,但每每因大臣们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可证御瓷水运入京的方式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仍未恢复。加之御器厂的生产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之后“役亦渐寝”,所以基本可以确定,从嘉靖九年(1530)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采用陆运的制度被一直沿用到明代御窑烧造活动结束。
综上所述,明代御瓷输京由水改陆始自嘉靖九年(1530),终于明代御窑烧造活动的结束。改革后的陆运线路段尚不确定,但至少包含了景德镇至池州段,之后再交由船运抵京。如此调整,明显比经昌江、鄱阳湖入长江到池州的行程短而且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避开了鄱阳湖一些复杂的水情,如老爷庙等地。但如果只有景德镇至池州段采取陆运,仍无法满足前文提到的隆庆时需要十二月、二月到京的时间安排,因为这时候是北方水路的封冻期。足见御瓷输京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中的难点与障碍十分复杂,而正是长期以来水运施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引发了嘉靖的这次改革。
二 运输方式调整之原因辨析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发现,嘉、隆、万三朝的御瓷输京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之所以用到“变革”一词,一方面同时代背景有关:“历经明初七十年的恢复、发展后,明王朝逐渐出现了保守和停滞的种种迹象⋯⋯嘉靖初立,以稳固皇权为动机和契机,君臣一度力图更新气象,采取一些力度较大的政治变革。”另一方面,这种时代精神反映到对御窑的管理上,也有许多锐意进取的举措。
诚然,嘉、万时期是景德镇民窑勃兴的时代,与之相反,御窑的各项管理制度均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例如对落选品处理方式较为草率、对工匠的管控变得松懈、对御用纹样的保护不再严密等,这种此消彼长往往被视作明代御窑走向消亡的前兆。但该时期的御窑依然有着数量巨大、样式丰富的订单,也就意味着皇帝对御器厂产品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热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御瓷运输方式的变革应该是当时社会变革需求的内容之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朝廷不会贸然选择一个从理论上来说速度更慢、载货量更少、耗费人力更多的运送方式,一定是为了规避掉水运的某些弊端,而这些弊端直接影响到了御瓷的进贡,所以进一步廓清瓷运调整背后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与水运相关的自然条件的影响
明代自永乐朝开始定都北京,皇宫需要的各类用品很多都来自遥远的中国南方,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贡品大多从内河进京,御瓷也不例外:“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这可能确实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得多。”御器厂产品需由昌江经下游的鄱江以及鄱阳湖、长江、京杭大运河运抵京城〔图三,图四〕,这一路上会面临许多来自河道以及季节带来的阻碍。

〔图三〕 御瓷输京水运路线图 (局部)

〔图四〕 御瓷输京水运路线图
以河道来说,虽然是内河,船只还是会经常发生搁浅、碰撞或倾翻的情况。例如鄱阳湖段自古在春夏潮涨时节便极难行驶,又尤以九江老爷庙段风浪极大,触及暗礁、搁浅等状况时常发生〔图五〕。又如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南京段,“有时在一个闸的出口或另一个闸的入口处,也会波涛汹涌,以致船只倾翻,全部水手都被淹死”。还有京杭大运河与黄河汇合的徐州段,“维持此段漕河航运,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 ,“黄河带给船夫的困难有三:泥沙淤积,易使船只搁浅;冬季,河水结冰;在急流处,河水咆哮⋯⋯”此外,京杭大运河其他河段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成化十四年(1478),太监汪直言:“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每遇西北风作,则粮运官民等船多被堤石、桩木冲破漂没,宜筑重堤于堤之东,积水行舟,以避风浪。”

〔图五〕 过滩
这一点在与御瓷相关的史料中也多有记载。万历三十四年(1606),江西巡抚许弘纲在奏折中提到:“今潘相议改船运,脱遇风波,谁为赔补?”万历三十五年,江西巡按史弼的奏折也提及:“江右由湖涉江沿二千里,始抵瓜步,道迂而甚险⋯⋯江西之瓷型,以便陆而之陆。今以脆薄之型瓷,犯波涛之颠播,一运有虞,必令地方赔补、窑户更造,竭膏髓而误上供,谁任其咎。”可见,水运也并非如想象中安全,甚至风险更高。
此外,御瓷水运的叫停还同季节有密切关系。史料中对御瓷运抵京城的时间有过一些记载,例如隆庆年间“限本年九月⋯⋯限本年十二月⋯⋯限明年二月⋯⋯”;而万历时期除个别极端的例证在冬季运送瓷器入京,“以五月十月到部”和清代分两次采用水运入京的方法相同。尽管这些时间节点并没有形成一个长期固定的安排,但运输时常发生在春夏以及冬季。春夏是南方的汛期,冬季则是北方河道封冻的时候:“一旦冬季来临,中国北方地区所有的河流都结厚冰,河上航行已不可能,车子则可以在上面通过。”如若是明代早期,御瓷运抵南京尚不算困难,只需克服汛期;明成祖迁都之后,御瓷则需要运抵北京,线路由南向北跨度极大,遇到来自自然的障碍也就多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陆运虽然耗费更多,但毕竟能够相对按时地将御瓷呈送到皇帝面前,所以这时御瓷运输在效率与稳妥之间选择了后者。
(二)更换船只的风险
按照明代的交通,御瓷走水路的行进路线应为:在景德镇昌江渡口装运上船,顺流而下至鄱阳湖,而后溯长江进入大运河向北抵京。明代地理学家郑若曾根据不同的行驶环境将明代船只大致分为四类:江船、海船、内河船以及湖泖船,那么御瓷水运分别要用到内河船、湖泖船以及江船。在船只的交接过程中(也称“接驳”),御瓷会被反复搬抬,加之这种工程往往是在起伏不定的水面进行的,很难避免跌撞等造成意外发生。
关于这点,清人唐英的奏折表述得十分清楚:“(御瓷)至解运到京,一路换船前进,几经扛抬搬运,未免动摇磕触,致有破损之件。”但清代并没有像明代一样废掉水运,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变通的运输方式:“将江西解淮上色瓷器九千三百七十五件,业于正月十二日由陆运运送进呈。尚有次色瓷器二万一千余件,奴才□造册籍,收拾装桶,由水路运送进京。”文献表明此时呈送御瓷是水、陆兼运,那些量少、高级的“上色瓷”采取不易破损的陆运,而“次色瓷”采用效率更高的水运。所以事实情况同前文的猜想是一致的,水运始终是运送大宗货物最高效、最经济的方式,清代这样的安排,既保证了精品瓷可以尽可能完整地运送到京城,又省去了一大笔陆运产生的开销。其实早在嘉靖时候,御器厂便有管厂官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是未被上级采纳。《江西省大志》载:“厂官议关策工部,是后凡钦限磁器陆运,至如部限磁器⋯⋯拣坚固座船,至饶州府河装载,由里河直达京师,委官乘传管解,刻期交卸,斯塞诏不至愆期,而夫马烦费南北均息矣。”
此外,唐英奏折显示大量上色御窑瓷器经昌江、鄱阳湖、长江、运河水运到淮安后,因为冬季的原因在淮安以北采用了陆运的方式,而更多的次色瓷器则仍然是装桶水运入京。说明清代御窑瓷器输京与明代一样,在冬季运输时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而不得不调整方案。所以清朝冬季水运到淮安而后采用陆运的处理方式就显得比较科学,这也使我们思考明代隆庆五年十二月、六年二月御瓷输京时需要考虑的内容,即在北方段不得不采用陆运方式。
(三)宦官督陶的废除
如前所述,御瓷采用陆运始于嘉靖九年。而为何刚好是在宦官督陶制度废除的时候,御瓷输京不再走水路?这与明代宦官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正德《饶州府志》卷二“公署”条载:“本府鄱阳县御器厂,即旧少监厅,在月波门外,宣德间创。每岁贡瓷器,太监驻此检封以进。”从宣德年间开始,御瓷都必须先运抵饶州府城鄱阳县月波门附近〔见图三〕,经由驻扎在那里的督陶宦官拣选查验,方可运往京城,而鄱阳县刚好处在昌江的下游,是御瓷走水路进入鄱阳湖前的必经之地。
明代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朝权极为深广⋯⋯无一时不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上”,御器厂也一直在他们的把持之下。督陶宦官往往由皇帝的心腹太监担任,大多是宵小之徒,他们为了迎合皇帝意趣而不计成本,严酷压榨御窑劳工,还假借采办之名,谋一己私利,地方官员又无法制约其权力,这一制度对江西地方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于是嘉靖朝废除了外派宦官督陶的制度,大多由地方官员担任,他们往往驻扎在景德镇。虽然之后宦官督陶仍时有发生,但不再在鄱阳县检封御瓷。《浮梁县志》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内监驻省,起运时驻镇”。说明此时御瓷发往鄱阳县的做法已不需要,陆运开始全面施行。从前引唐英奏折可知,清代陆运瓷器入京的线路段是在淮安关以北,这和《江西省大志》记载的明代御瓷陆运局限在景德镇到池州段又有不同,可见御瓷陆运至京的线路段、原因等情况绝非简单。
三 结语
明代御器厂的烧造活动素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得益于丰富的传世品以及景德镇御窑旧址考古出土的大量材料,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器物本身或御器厂内部的遗物、遗迹,虽然也呈现着十分丰满的面貌,但对于如御瓷输京这类瓷器烧造之外的管理方式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史料,结合辩证分析,初步厘清了明代晚期御器厂产品进京的运输方式以及其在嘉靖九年发生变革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晚明御瓷运输方式的变革折射出一些更为深刻的内涵。一方面,明代朝廷对御窑的管理并没有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在嘉万时期全面走向崩塌,而是依然有其独到之处:尽管陆运速度慢、耗费大,但有效地避免了瓷器破损情况的发生,还避开了沿途水情的干扰,从而成为了明代晚期御瓷运输方式的不二之选,但陆运一事绝非从景德镇到池州段这样简单。明代朝廷对管理御窑所作出的思考与尝试,也为清代的改革和新法的施行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嘉靖皇帝承继大统后,在杨廷和、张璁等人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又务实的变革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对宦官势力进行削弱,宦官督陶的革除与御瓷水运的停废也正发生在此时。通过前文的史料可以看到,宦官反复以各种理由提议恢复水运,与之相反,文官则每次都极力反驳,这固然是因为水运的一些不利的客观因素所导致,但更是双方势力围绕着御用器物的控制权所展开的角力与博弈。
此外,由于笔者学术水平的不足,本文尚存在不少挂一漏万的地方,最大的遗憾是始终没有厘清御瓷陆运进京的具体线路段,希望拙文能够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对该话题更进一步的探讨。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