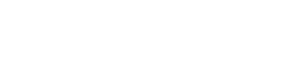在此前“革命时代的……建筑”中,我们从一系列的问题开始:建筑与革命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果存在,那是怎样的关联?或者说,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形成关联?总体上来看,建筑介入社会的只能是改良,因为大部分情况下需要既定的意识形态底色和相关政策的支持,而另一种方式是诉诸于抵抗的姿态,比如“批判地域主义”的提出,以“地域”的多元主义去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标准化。然而,这一提案内部存在的矛盾性在于,所谓的风土施加于本地决策上的权力同样也是无处不在的。由此,抵抗更看重的是文化和意识的效果,却很容易忽略伴随而来的经济自治的要求,尤其是在冷战之后的地方政府和各个民族国家那里。反观所谓“革命”的建筑,更值得关注的是维也纳艺术史学家埃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形成这一议题的时代背景。从根子上说,考夫曼之所以要对布雷、勒杜和勒克的遗产重新评估,其动机是因为他观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二十世纪初之间结构上的同源性。建筑和革命两者的关系并不遵循互为因果模式的直接对应关系。换言之,建筑本身既不会带来革命,也不会阻止革命的发生,反之亦然。更不能认为它们同步地决定了彼此。之所以能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同构性,是因为它们共同地投身到了革命的时代精神之中。事实上,是反抗传统的精神激励了理性时代所有的进步建筑师。当然,即使这种激进的创新精神只不过是现实历史动力的意识形态反映,我们考察1789年和1917年前后革命建筑时,仍然可以从中发现某些突出的共通点,比如几何化的形式、简洁、清晰、理性,更具普遍性的概念等等。本次推送的是革命建筑所涉及布雷和勒杜的部分研究案例,并引向另一些新的议题。
贝桑松剧院室内|Claude-Nicolas Ledoux|1784 前身即来世|理性和革命时代的基进资产阶级建
前身即来世|理性和革命时代的基进资产阶级建
革命与建筑的讨论,可以始于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一场大革命和那些建筑的想象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这种关联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如果有关联,那么历史上曾经是怎样的关联?换成当下的语境,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形成关联?此前我们做过一些横向的扩展分析:总体上来看,建筑介入社会的方式只能是改良,大部分情况下需要既定的意识形态底色和相关政策的支持;而另一种方式是诉诸于抵抗的姿态,然而这种抵抗究竟是看重文化和意识的效果,还是引向经济与政治的实质行动,还有待根据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做出分析。
让我们暂时回到历史的原点,也就是维也纳艺术史学家埃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他所身处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初期,并进而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同源性。埃米尔·考夫曼研究了三位建筑师的作品,分别是艾蒂安-路易·布雷[Étienne-Louis Boullée, 1728-1799]、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 1736-1806]和让-雅克·勒奎[Jean-Jacques Lequeu, 1772-1837],这三位都可以被看做是乌托邦或空想的建筑师。也就是在1789年,光荣的法国大革命这一年前后出现了这些建筑幻想,又恰好都是法国人,这或许并非巧合。
除了是建筑师之外,我们还应该把他们称为当时代的思想者。他们图纸上显现出来的理念,反映的正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哲学中一些最为基进的思想,是对理性的崇拜,并投身于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重理念之中。毋庸置疑,他们在那个时代所绘的建筑图纸,提出的城市构想是最为雄心勃勃和最具革命性的。他们设想的那些颇为奇幻的建筑物,绝对是无法建造的。无论是按照他们那个时代的技术标准,还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标准,都可以说是无法建造的。
让我们着重看一下前两位建筑师,布雷和勒杜。其中布雷还是著名的理论家和教师,传授十八世纪由法国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培养出了他们那个时代一些杰出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比如法国的让·夏尔格林(巴黎凯旋门)、亚历山大-泰奥多·布隆尼亚(巴黎布隆尼亚宫)和让-尼古拉-路易·迪朗(《建筑学课程概要》)。布雷和勒杜自己实际建造出来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更为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范围内的展开的,这可以证明他们对这种风格的把控力是非常全面的。除了推崇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风格之外,他们还从诸多的风格中获取主要的灵感。
布勒和勒杜这两位建筑师把精力大多放在了乌托邦式的图纸上。可以说,他们绘制出的那些不可能实现的建筑图,完全把维特鲁威和阿尔伯蒂强调的可行性和实用性的论述放在了一边。由此,布雷和勒杜都打上了他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烙印。那是一个科学、知识和政治革命的时代,他们遭遇到基进的思想,并见证了革命的事件,这都给他们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他们眼前形成,在这个新世界里,无限的可能性,都有可能出现。
理想之家|勒杜|1770 牛顿纪念堂|布雷|1784
牛顿纪念堂|布雷|1784
布雷和勒杜摒弃了新古典主义建筑所依据的众多装饰和柱式的原则,重新调取极其简化的几何形状——球体、方体、去除了装饰的拱门等等。布雷甚至还在他的大都市教堂的草图中 [图A5、A6] 加入了一个长方形的光眼,如果这样一个形状也可以称为“光眼”的话。他们的作品去除了任何装饰性的特征,而是以质朴的深刻性示人。布雷的牛顿纪念碑 [图A3、A4] 和勒杜的理想之家 [图B1] 是这两位建筑师运用球体结构的案例,这种设想在当时的确是令人震惊不已的。
布雷设计的许多空想建筑都是为了纪念启蒙运动中的伟大人物以及概念。他最为知名的就是提出了纪念牛顿的建筑方案。除此之外,1794年,就在罗伯斯庇尔公布“至高无上崇拜”之后,布雷还设想了献给“至高无上者”的礼物,一座纪念堂 [图A1、A2] 。布雷将这一概念具体化了,为此他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他感慨道:"这是一座敬拜至高无上者的建筑!这确实是一个呼唤崇高理念的主题,建筑必须赋予其特征”。
而勒杜的际遇则不同,他在旧制度下曾经为贵族造过房子,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在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数年。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对罗伯斯庇尔崇拜这些雅各宾派的创新另有一种黯淡的看法。勒杜绘制的一些建筑物在意义上甚至要比布勒对牛顿或至高无上者的赞颂更加抽象,也更不可能被建造出来。例如,他在1804年出版的作品版画汇编的最后一幅图中,勒杜描绘了一个云的宇宙,漂浮在Chau市墓地上空 [图B10]。
这座城市最初也是由他帮助规划的。那是一个微型的地球,在云层上被一些较小的行星包围着,这些行星在轨道上环绕着它。在没有支撑物的情况下悬浮在空中。它们几乎就像一组空气静力学的球体,与蒙戈尔费兄弟在1783年推出的著名热气球并无二致。勒杜通过这一地心的模型,似乎给予埋葬在墓地里的居民一个托勒密式的来世。
然而,并不只有勒杜想到了来世。1794年,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在热月运动中被处决后,布雷也感到革命被背叛了。由此,他的情绪也越来越病态,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思死亡和埋葬的理念。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幅可怖的景象:一道光,惨白至极,黑暗中,东西散落开去,一堆一堆。大自然,就在那里,在哀悼中,赫然闯入我的眼前。墙壁上,装饰都剥落了......那些材料吸了光亮,将创造出黑黢黢的建筑,用更加黑沉的阴影,把它勾勒出来。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布雷为他的另一件无法实现的杰作——《死亡之殿》绘制了草图。它的外部是金字塔形的[图A7],内部包裹着球形的坟墓[图A8]。然而,布勒更让人念念不忘的可能也是最黑暗的。他早期的“牛顿纪念碑”,内部充斥着人工的光线,而他重新想象的内部则显示出坟墓般的黑暗,在永久的黑夜包裹下,这一巨大空腔的底部显得藐小无比[图A10]。
1800年之后不久,整个事态的发展开始偏离了布雷和勒杜业已显现的理念,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原本那种激情的本性流露,现在变成了形式文章。布隆代尔在其晚期的著作中,仍旧体现出法国古典主义的教义。仅仅时隔三十年不到,从“建筑学课程概要”开始,迪朗 [Jean-Nicolas-Louis Durand,1760-1834] 的思想在帝国以及此后的时期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在巴黎皇家理工学院的席位上宣布了自己的准则,在所有的关键点上都与布隆代尔有分歧。“课程概要”以猛烈攻击两件著名的巴洛克艺术作品开篇,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和巴黎的先贤祠现在都成了反例。布隆代尔还不忘提醒人们切莫一味地侧重于平面的几何,而忽视了透视的功用,但在迪朗看来,只有在平面的基本图式中,人们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牛顿纪念堂(重绘)|布雷|1795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未完待续▶议题布雷与勒杜这两位建筑师虽然同处一个时代,但是由于际遇不同,他们各自侧重的创作方向也不尽相同;布雷集中在反映新的社会理想的纪念物上,而勒杜将建筑不断生发为用以规范新的社会发展的方法;那么,具体到图纸创作与分析上,这两者之间又有哪些特定的差别?同样是作为这一时代的纸上建筑师,乔瓦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和上述两位建筑师有哪些区别?为什么二十世纪70年代的塔夫里在讨论先锋派建筑时,更看重皮拉内西的创作?1789年和1917年前后革命建筑的从形象上来看具有某些共通点,比如:几何化的形式、简洁、清晰、理性,更具普遍性的概念等等;如果说正是出于艺术概念的逻辑,才可能带来近似的结果,而并非巧合的话,那么,如何理解对俄国世纪先锋派的建筑形式的“借用”?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Étienne-Louis Boullée,1728-1799艾蒂安-路易·布雷这位法国的建筑师,理论家和教师,生于1728年2月12日,卒于1799年2月6日。布雷最初想成为一名画家,但后来遵从了父亲的意愿,转向建筑。他曾师从J.-F.布隆代尔[J.-F. Blondel]、格尔曼·博弗朗[Germain Boffrand]以及J.-L.勒热[J.-L. Legeay]。19岁时,他就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在十八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设计了多座巴黎城市豪宅,其中最著名的是布鲁诺伊酒店[Hôtel de Brunoy, 1774-79年]。尽管布雷的作品都具有创新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但是作为一名教师和理论家,他的影响力却是经久不衰的。亚历山大-泰奥多·布隆尼亚[Alexandre-Théodore Brongniart]、让-弗朗索瓦-泰雷兹·夏尔格林[Jean-Franƈois-Thérèse Chalgrin]、让-尼古拉斯-路易·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和路易-米歇尔·蒂博[Louis-Michel Thibault]等大师都曾经在他那里工作过。布雷执教总共长达50多年。在布雷那些重要的公共纪念碑的理论设计中,他试图通过建筑形式来激发观者的崇高情感,这些建筑形式暗示了自然世界的崇高、浩瀚和令人敬畏,以及创制世界的神圣智慧。同时,他也深受同时代的人对古代,尤其是埃及古迹的狂热影响。布雷成熟期作品的显著特点在于,他将古代作品的几何形式抽象为一种新的纪念性的建筑概念,这种概念既具有古典建筑的沉稳、理想之美,又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在他的名篇“La Théorie des corps”中,布雷研究了几何形状的特性及其对感官的影响,将“与生俱来”的象征性赋予了立方体、金字塔、圆柱体和球体,而球体被看作是理念形态。在一系列的公共纪念碑项目中,布雷将他的理论赋予了想象的形式,最终在1784年设计了一个巨大的球体,作为纪念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的纪念堂/墓。纪念堂的内部是一个代表着宇宙的空心球体。
布雷依靠引人注目、独具匠心的光影效果,给几何形状赋予了生命。他还强调建筑的神秘性,经常将结构的一部分埋入地下。这种“诗意”的建筑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我们也可以从布雷大量使用了象征主义的作品中看到。例如,他设计的市政宫[Palais Municipal]坐落在四个基座式的守卫房上,表明社会是由法律支持的。布雷对观者心理的强调是他的“Architecture, essai sur l’art”的主要主题,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版。由于他倾向于提出宏伟的方案,他被批评为自大狂,但这些方案应该被看作是具有远见的计划,而不是实际的项目。布雷希望能够创造一种特别的、独创的建筑,以适合理想的新社会秩序。而他的这一愿望也预示了二十世纪的建筑界的类似关切。
▼ 图A1、A2|Monument to the Supreme Being|至高无上纪念堂|1780
 ▼图A3、A4|Cenotaph for Newton|牛顿纪念堂|1784
▼图A3、A4|Cenotaph for Newton|牛顿纪念堂|1784
 ▼图A5、A6|Metropolitan Cathedral|大都市教堂|1784
▼图A5、A6|Metropolitan Cathedral|大都市教堂|1784
 ▼图A7、A8|Temple of Death|“死亡之殿”金字塔式塔身|1795
▼图A7、A8|Temple of Death|“死亡之殿”金字塔式塔身|1795
 ▼图A9|Temple of Death|另一版“死亡之殿”方案螺旋塔|1795
▼图A9|Temple of Death|另一版“死亡之殿”方案螺旋塔|1795 ▼图A10|Cenotaph for Newton|牛顿纪念堂(重绘)|1795
▼图A10|Cenotaph for Newton|牛顿纪念堂(重绘)|1795 Claude-Nicolas Ledoux,1736-1806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这位法国建筑师,生于1736年3月21日,卒于1806年11月19日。他的设计风格兼收并蓄(折衷主义),富有远见,与革命前新生的社会理念息息相关。勒杜师从J.-F.布隆代尔[J.-F. Blondel]和L.-F. 特劳尔德[L.-F. Trouard]。他在咖啡馆项目中富有想象力的木制品设计让他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很快他就成为了一名时髦的建筑师。十八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他为法国的上流社会设计了许多创新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私人住宅。那些作品幸存的为数不多,包括了霍夸尔亭[Hocquart Pavilion, 1764-70],诺曼底的贝努维尔城堡[Château de Bénouville,1770],还有在鲁夫西恩著名的杜巴利夫人[Madame du Barry]城堡[1771-73]。在十八世纪70年代中期,勒杜开始在阿尔凯特瑟南斯[Arc-et-Senans]的规划新建一座盐厂及其周围的城镇。他为居住区设计了一个放射状的同心圆规划,工人们的住所环绕着位于中央的采盐场。尽管最终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工程,但存下来的建筑显示了勒杜对立方体和圆柱体的惊人简化,创造了粗犷的古典建筑类型。
Claude-Nicolas Ledoux,1736-1806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这位法国建筑师,生于1736年3月21日,卒于1806年11月19日。他的设计风格兼收并蓄(折衷主义),富有远见,与革命前新生的社会理念息息相关。勒杜师从J.-F.布隆代尔[J.-F. Blondel]和L.-F. 特劳尔德[L.-F. Trouard]。他在咖啡馆项目中富有想象力的木制品设计让他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很快他就成为了一名时髦的建筑师。十八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他为法国的上流社会设计了许多创新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私人住宅。那些作品幸存的为数不多,包括了霍夸尔亭[Hocquart Pavilion, 1764-70],诺曼底的贝努维尔城堡[Château de Bénouville,1770],还有在鲁夫西恩著名的杜巴利夫人[Madame du Barry]城堡[1771-73]。在十八世纪70年代中期,勒杜开始在阿尔凯特瑟南斯[Arc-et-Senans]的规划新建一座盐厂及其周围的城镇。他为居住区设计了一个放射状的同心圆规划,工人们的住所环绕着位于中央的采盐场。尽管最终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工程,但存下来的建筑显示了勒杜对立方体和圆柱体的惊人简化,创造了粗犷的古典建筑类型。
他对城镇的布局既促进了经济生产,又确保了工人们健康快乐的生活条件,也预示了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和其他十九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类似的规划努力。勒杜的贝桑帕尔松剧院[Theatre of Besançon,1771-73]是一个革命性的设计,为普通公众和上层阶级提供了座位。他在十八世纪80年代设计的私人住宅具有极其亮眼的古怪特征,包括奇怪的布局,不连续的立面,以及多立克建筑元素的惊人运用。勒杜职业生涯最后阶段最重要的公共项目是设计了60个位于巴黎城门的收费站。他把原本并不起眼的海关办公室变成了一系列具有纪念意义的大门以及其他称为“巴黎之门”[Portes de Paris]的建筑。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四年间(1785-1789年)实际建造的50座这样的收费站(或称为“关卡”)中,只有四座幸存下来,其中包括著名的拉维莱特站[Barrière de la Villette]。在这些建筑中,勒杜把他对方正、巨大的几何形状的兴趣发挥到了极致,用粗犷的砖石和多立克柱建造了圆形大厅、希腊神庙、门廊和拱形尖顶。然而,这些建筑的造价对国库来说是巨大的亏损,1789年他被辞退了。
后来这些建筑也在大革命期间被愤怒的纳税人暴民推倒。勒杜本人在恐怖期间被捕,这一事件和他几位家人的死亡结束了他的建筑师生涯。出狱后,他利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里编撰了“L’architecture considérée sous le rapport de l’art, des moeurs et de la législation, 1804”(从艺术、习俗和立法的角度考虑建筑”),其中包含他自己作品的版画。勒杜可以说是十八世纪晚期法国最多产、最具独创性的建筑师。然而,他简洁有力的几何形状设计似乎吸引不了后人,十九世纪的大肆拆除和破坏只留下了很少的几处勒杜的作品。1982年,阿尔凯特瑟南斯的盐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遗产。▼图B1|Ideal House|理想之家|1770
 ▼
图B2、B3|
Théâtre de Besançon
|
贝桑松剧院室内
|1784
▼
图B2、B3|
Théâtre de Besançon
|
贝桑松剧院室内
|1784

 ▼
图B4、B5|
The Ideal City of Chaux
|理想之城
|
1804图纸
▼
图B4、B5|
The Ideal City of Chaux
|理想之城
|
1804图纸

 ▼
图B6、B7|
Oikema: House of Pleasure
|
1804年图纸
▼
图B6、B7|
Oikema: House of Pleasure
|
1804年图纸

 ▼
图B8|
The Country House
|
1804年图纸
▼
图B8|
The Country House
|
1804年图纸
 ▼
图B9|
The Cemetery
|
1804年图纸
▼
图B9|
The Cemetery
|
1804年图纸
 ▼
图B10|
Elevation of the Cemetery
|1804图纸
▼
图B10|
Elevation of the Cemetery
|1804图纸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