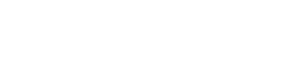现在的艺术评论是否过于正面了?难道“负面评论”是唤醒这个沉睡景象的良药吗?批评家Sean Tatol在上月为《观点》(The Point)撰写的一篇名为《负面批评》(Negative Criticism)的文章就是这样论证的。外界对文章的评价很高。这确实是一篇具有使命感的文章,我也希望这样的文章能更多一些。不过,Tatol立场的优缺点都值得探讨——事实上,他非常清楚地阐述了通过辩论来确定利害关系的好处。最初,Tatol是通过独立刊物《曼哈顿艺术评论》(Manhattan Art Review)一举成名的。
正如他在《观点》杂志上说的那样,这份刊物最著名的是“批评家之角”(Kritic's Korner,这是一个短评栏目,仿照摇滚乐批评家Robert Christgau传奇的音评栏目“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而来)。“批评家之角”的阅读体验非常有趣,Tatol的短评将大量的思想和情感压缩在短短几句切中要害的话中。通常,他的评论都带有明显的负面色彩,对艺术作品的评分从一星到五星不等,负面倾向非常明显。无论你如何看待Tatol的观点——人们对他的观点通常都有很多看法——《曼哈顿艺术评论》的成功都是值得兴奋的。因为它除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媒体栏目外,还让人们开始讨论本地小型画廊里的一些非著名的艺术家展览,这非常了不起。
 音乐评论家Robert Christgau在纽约Entermedia Theater,1978年10月17日,图片:Photo by Ebet Roberts/Redferns
音乐评论家Robert Christgau在纽约Entermedia Theater,1978年10月17日,图片:Photo by Ebet Roberts/Redferns
《负面批评》是一篇为《曼哈顿艺术评论》辩护的长篇文章,认为《曼哈顿艺术评论》不仅仅是娱乐性地记录“过去”和“现在”。下面是Tatol的阐述:
撰写有关艺术的文章可以有多种目的,但任何分析的背后都潜藏着评判问题。大多数当代艺术写作都将阐释作为回避质量问题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艺术本身不好,阐释就不可能被认真对待。
回避评价的批评家的作品可能较少引起争议;也许他们会保护自己,避免说出让后人听起来尴尬的话。但代价是,他们无法帮助读者学会如何判断艺术或理解艺术,而这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
在对特定艺术展的评判中,我传达了我对艺术(或优秀艺术)的理解,我只希望这对其他有兴趣培养自己品味的人有所帮助。《曼哈顿艺术评论》的目标是提供一种奇思妙想,以抗衡当前盛行的艺术和艺术评论惯例,否则,这些惯例可能会因贪婪、冷漠和口号化而劝人愤世嫉俗。
在这篇文章中,Tatol暗示了造成真正具有批判性的艺术批评之所以会缺席的各种可能原因,它们包括:其一,艺术中的商业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平淡无奇的“推销”的默认;其二,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反感对艺术质量的评判(他称之为“主观绝对主义/subjective absolutism”);其三,进步的批评家倾向于根据艺术所传达的信息对其进行积极的评判,《纽约时报》批评家Holland Cotter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原因中,Tatol最强调的是第二点(顺便提一下,这三点与上文提到的“贪婪、冷漠和口号化”正好是对应的)。即使这些原因更多的是结论而非分析,但它们确实表达了一些真实的东西——那种艺术圈看起来“好像很高雅,却又玩世不恭”的、令人腻烦的氛围。我知道有一些人在策划着发起一个叫“差评”(Bad Review)的东西,诚然,这种行为其实既不新鲜也不稀奇——20年前,批评家Raphael Rubinstein就在《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上写过《静悄悄的危机》(A Quiet Crisis)一文,另一位批评家Jed Perl在去年刚刚出版的著作《权威与自由》(Authority and Freedom)中也提到了很多类似的内容——但Tatol的宣言显然道出了人们心中的挫败感。然而,我思考的问题是,“负面批评”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甚至“去质疑这些判断”是否又能真正全面地反映问题的关键所在?接下来,让我来解释一下。
 有的尖锐 有的陈旧
有的尖锐 有的陈旧
为消费者服务仍然是专职批评家工作的专业基础;忠实性、证据等仍然是衡量其价值的标准,但高度的批判性在应用于大多数普通作品时变得错位、不相称。尽管如此,批评家仍有义务去做更多的事情。对一个有思想的成年人来说,只陈述简单的事实——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确实不错,这个完全不行——这不应当是一天的工作。有些批评家声嘶力竭,另一些却只是在说陈词滥调。
然而,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倾向是原地踏步,只是一味地夸大,假装每天都是危机——最重要的、第一的、最好的、最糟糕的、最差的、最深刻的等等——既然我们是在用“超级术语”(superlatives)打交道,那么就该担起责任,这是专职批评家们首要的、最明确的职责之一。
我喜欢这段话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它说出了“判断”这件事本身并不难 (“对一个有思想的成年人来说,这不应当是一天的工作”) ,过度肯定和过度否定都可能是机械的条件反射。不过,当我们不再谈论专职批评家,这种认知方式就不会受到影响。 (Tatol认为,“批评家之角”之所以采取短评形式,是因为他认为“定期发表一些轻松甚至轻率的、随心所欲的评论会吸引更多关注”。)
 Renata Adler在纽约,1987年6月10日,图片:Photo by Ron Galella, Ltd./Ron Galella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Renata Adler在纽约,1987年6月10日,图片:Photo by Ron Galella, Ltd./Ron Galella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Let People Enjoy Things”表情包,图片:via KnowYourMeme
“Let People Enjoy Things”表情包,图片:via KnowYourMeme
 客观地主观
客观地主观
我喜欢Adler那段话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它蕴含着一种“诚实的智慧”,说明了在进行定期评论报道时存在的真正困难:事实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不好,大多数东西是OK的,但也只是OK而已——有点意思,但又不是很有意思。因此,如果你不得不写,或强迫自己写,你将面临一个不幸的两难选择:要么你尽职尽责地书写它们(这符合你的职责要求,但会让人疲惫不堪),要么你系统地用文字“假装每天都是一场危机”,这要有趣得多,但又会显得很夸张。我确实曾听到有人说:“那么,你难道不应该为‘有这么多无聊艺术’的这个事实本身而义愤填膺吗?”我的答案是当然,如果你认为这是对你时间和精力的合理利用的话。
但过度批评也容易导致人们的过度推崇,这不也助长了部分平庸的作品获得成功吗?在我看来,Tatol在《负面批评》中所阐述的理论的奇特之处在于,虽然他谴责当代艺术写作中的“主观绝对主义”,并建议人们应该追求“客观”的标准,但他不断通过强调自己的主观性和自足性来削弱这一点——例如,“批评家不应被要求达到无懈可击的标准,而应被要求达到内在的一致性”,或者“这些判断的价值不在于它们绝对正确或错误,而在于它们是批评家感性的结晶”。这种“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如何玩游戏”的姿态捕捉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强烈的观点之所以被关注,有可能只是因为它们态度强烈。通过引发辩论,它们迫使人们向自己和他人澄清自己为什么要喜欢/不喜欢某些事物。尽管如此,我认为在Tatol的文章中,强调敢于对作品的质量做出判断,是为了说明判断的基础是什么。拥有特别自洽的逻辑和感性本身是好事,但如果不能用“无懈可击的标准”来要求批评家,那么读者有理由质疑批评家错了吗?依据是什么?
 “批评家之角”一瞥
“批评家之角”一瞥
 在苏富比“现当代非洲艺术”专场中,一位画廊专家站在阿莫科·博弗作品《无题》前,图片:Photo by John Phillips/Getty Images for Sotheby’s
在苏富比“现当代非洲艺术”专场中,一位画廊专家站在阿莫科·博弗作品《无题》前,图片:Photo by John Phillips/Getty Images for Sotheby’s
Tatol寥寥数语,就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点:博弗标志性的手指画技法有其优点,但还不足以让人一次又一次地对其组作品产生持续的兴趣;除此之外,他认为这些画看起来毫无生气、缺乏新意,像是流水线生产。我认为这篇评论对博弗的定性略有偏差,因为他笔下高度加工的皮肤纹理与简化的其他元素之间的对比显然不仅是为了省时间,而且是为了营造某种引人入胜的对比感——只是最终的效果可能没那么引人入胜。所以这段短评似乎既是对博弗画作弱点的直击,也是对造成这些弱点的分析,使这段短评的利害关系一目了然。
纽约的艺术场景非常庞杂,但在庞杂之下,参考点却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批评家可以假设很多,工作速度也很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说到点上。而我也不难发现,在Tatol的判断中,也有偏离轨道的地方(顺便提一下,在他的体系中,1.5星大概是介于“客观的不行”和“他个人觉得不行”之间)。比如他对摄影师Barbara Ess的作品是这样评价的:“我认为这应该是纽约朋克摇滚乐的一种运作方式,而我对这种方式并不熟悉。所以我绝对不喜欢!”
 Barbara Ess,《Girl in Corner》,1997-98,图片:Photo by Ben Davis
Barbara Ess,《Girl in Corner》,1997-98,图片:Photo by Ben Davis
 “Barbara Ess: Inside Out”展览现场,图片:Image courtesy Magenta Plains
“Barbara Ess: Inside Out”展览现场,图片:Image courtesy Magenta Plains
当然了,没有人必须要喜欢任何东西。但就像我说Tatol对博弗的评论是对的一样,我也可以认为他对Ess的评论是错的。它没有说清楚作品的样子,或它们想要做什么,只是随意地以个人化的反感情绪(“我绝对不喜欢!”)来否定它们。而这几乎是当强烈意见或单纯的负面评论脱离理论基础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它会显得像是匆忙且站不住脚的否定。
 消极空间
消极空间
归根结底,我无法将Tatol在《负面批评》中对批评所起作用的崇高理论——作为“智力成熟的缓慢发展”的榜样——与他在“批评家之角”中大量批评背后的权衡之感联系在一起。在《曼哈顿艺术评论》内部,缺乏对个体形式的持续参与和流水线式的内容被指责为“导致了许多糟糕的艺术思考”。除了Tatol文章中提到的“贪婪、冷漠和口号化”之外,我还想加上第四个原因,即“媒体环境的堕落”。既然Robert Christgau的乐评是超凡脱俗态度的标杆,那么对其他人而言,使用他这种评论模式的要求之高就不言而喻了。摇滚乐学者Simon Frith曾解释过Christgau为其乐评所付出的诸多努力:“编辑会议都非常具有技术性。在证据和准确性方面,Christgau甚至比我的任何导师都更严格。他对好文章的痴迷程度非常高。”对一位写作者而言,培养自己的“声音”需要时间,要接触各种不同形式的写作——文学、哲学、艺术史——从而形成独特的视角,让人们愿意阅读。此外,还需要花时间去欣赏大量的艺术作品,并在众多的艺术作品中寻找值得书写的那些。把每场展览作为一个单独的事物来思考,找出足够的信息,并对作品做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这都需要时间。
而且写作也需要时间。所有这些方面都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压力。Sean Tatol的《曼哈顿艺术评论》之所以能吸引大量关注,部分原因在于对非著名的本地展览的定期评论报道越来越少。与此同时,随着媒体传播速度的加快,投入较少的文化写作形式也大量涌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写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流传得更广的可能,但投入到单篇写作中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却越来越少。这让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冗余感和单薄感。正是由于这种背景,我希望当代艺术批评理论能比《负面批评》更有基础,以区别于它所呼吁的、已成为这个时代定义的那种“不那么投入”的写作类型——只想着吸引眼球、用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或蹭热点。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背景,我认为Tatol的呼吁传达出了更大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超越了艺术评论这个领域本身,这也是为什么它让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来思考的原因。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