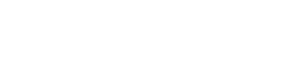可有一批中国超当代艺术家却执意从家乡的过去汲取内容,在故土中摸索属于自己的方法。
闫冰(b. 1980 甘肃)对刻画粮食的执着,可以追溯到甘肃天水的村庄与土地 。生活在戈壁与丘陵分割线上的人,对于“自然造物”的神圣有与生俱来的领悟力。他对基础性食物充满敬畏:“它们不是美食,也不是为了享受而生的,仅仅是一些帮助人维持生存底线的存在之物。”2009年,他做了一件名为《粮食》的装置,把家乡的泥土和麦壳制成一堆土豆的形状。此后的十来年,土豆、蘑菇、馒头和农具是他绘画的核心主题。
王光乐(b. 1976 福建)的“寿漆”源自福建松溪的乡俗。 当时南方还兴土葬,老人会在一个微妙的时刻给自己准备一口棺材,每年择日为自己的寿材刷一遍红红的大漆。“一年一遍,幸运的话,可以为自己刷上几十遍。”他曾自述:“我的观察是:老人并不害怕,而是审慎——简直就不是给自己料理后事。”想必很少有人会考虑乡俗对创作抽象艺术的贡献,可正是在这种地方传统的启发下,王光乐决定在画布上一层层地涂抹颜料,层与层之间颜色变化而呼应,不断覆盖,直到无法落笔。如履薄冰的控制力勾勒着每一条边缘的庄严;而色块中部那些看不见的大面积涂抹,是肆意挥洒的性情。
从上世纪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来的小城辽宁丹东,与日本同纬度、与朝鲜仅有一水之隔。生在这里的贾蔼力(b. 1979 辽宁)把鸭绿江的水、日式榻榻米拆掉后留下的建筑结构,以及身处寰宇之中的芸芸众生对救赎和重生的渴望,化作笔下的“莽原”和“疯景”。
“家乡对于一个艺术家的自我建设,就像胎教对于一个婴儿的未来一生。”《福建:最好的胎教》(2012)里写道。艺术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他们内心秘境的重要部分:榕树给了闽人独木成林的态度,海洋教会他们独自面对风浪的哲理,这片土地上自然的丰富性与生命的偶然性使乡人忘却了死亡的恐惧,也使王光乐在看似机械化的重复中顿悟时间堆叠的意义。而高瑀(b. 1981 贵州)画的“钟馗”和“李白”是西南人独有的玩世不恭、逍遥自在,如川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唱词“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艺术家把它总结为“小丑精神,说白了,就是嘲讽世界,嘲讽自己,所以我嘲讽的既是世界,又是我自己,因为我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可能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速度过于炫目,以至于一些从地理和历史中生发出的地方特征变得越来越模糊,消失的速度令人有些措手不及。日趋同质化的资源,像一个巨型的诱饵,在“飘香”的表象下潜伏着空洞和危险。而那些还没有被忘掉的、来自家乡的思维方式、文化和经验,对于创作者来说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珍稀。
它或驻在心里、或等着游子回来,总有些隐秘而亘古的东西还在那里 ——比如风沙注入闫冰血液里的东西。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土豆像首次登台领奖的文学家,在古典主义笔法下质朴而肃穆,同时,面对这迟来的凝视又难掩错愕;蘑菇伞丝绸般高贵的光泽周围是晦暗的阴影,似乎总有一丝苦楚说不出口。带着这些悬宕于心的东西,两年前他决定从城市回到故土探寻答案,他踏上了杏林湾周边地区的戈壁。那里的野菜日夜经受风沙的洗礼,却意外地比土豆这种引自外乡、人工培育的口粮多了一分自然和温和。正如他同年的个展标题:“突然,一切清晰了起来”。他在媒体采访中谈到:“我在故地走入了新的精神世界。新的感受和领悟带我逆向穿过了原有的认知,犹如从一片云影里走出。”
《中国的新艺术:正在崛起的一代》的作者芭芭拉·博莱克曾说,与前辈相比,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更加国际化和个人化,“当你看它第一眼的时候,你很难确定那个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的确,中国超当代艺术家不像85新潮的前辈或者更久以前的艺术家那样,热衷于政治话题或地方性团体。像N12这样因同窗而识的艺术小组林立,可新的西南艺术群体恐怕不会再有。但今天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当你看第二眼,会发现原来他们不是笼统的“中国超当代艺术家”,他们本身想表达的也不是文化对比视角下的“中国感受和中国概念”。尽管当代资源越来越同质化,可在广袤的土地上生长出的丰沛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源泉,为创作的持续和多元留下了无穷宝藏,等待发掘。
陈飞(b. 1983 山西)认为这一代人在文化建设上要强调自身文化属性:“艺术的表现方式、媒介、材料无非就这么多种,但是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现东西方的这种文化进入点的差距是越来越明显的,就是我们呈现的面貌有可能一样,但是你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逻辑观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要强调的。”
面对艺术史尚未给予定论的75后艺术家,如今外界似乎更在意他们的毕业院校、被谁收藏过、参加了多少次机构展览、甚至是有多强大的流量效应。尤其在艺术品交易中,故乡,几乎是“最不值钱”的线索。在大部分拍卖行官网的拍品基础信息页,你看不到出生地。多数时候,它甚至比作品的装裱方式和流转经历(provenance)还次要。
诚然,把一个人的出生、一个地方的记忆说给全世界听,激发他乡人凝视它、甚至拥有它的欲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艺术家意识得到,那些活跃在全球市场的艺术推手、经销商也看得清。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在艺术市场趋向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古典大师的作品仍只流通于纽约和伦敦,而中国书画的市场始终集中在北京。再参考欧洲的现代与印象派艺术,有一批风俗画家(genre painter),把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和节庆习俗作为描绘的主要对象,他们很少出现在伦敦和巴黎以外的拍卖市场,即便曾经风靡过,如今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也难与同期的莫奈、梵高匹敌。
可有趣的“异象”是,今天这批跳出全球艺术市场“数字时代”“超扁平”(superflat)之热流,尝试从故乡的地理风貌与历史文化中寻觅自己的中国超当代艺术家,非但没有被视为局限或过气,反而意气风发,打开了某种新格局——前文提到的贾蔼力、王光乐、闫冰、陈飞和高瑀,还包括黄宇兴(b. 1975 北京)、陈彧君(b. 1976 福建)等,都是过去两年内公开市场累计成交额前20的中国超当代艺术家。他们的展览经历、代理画廊、观众、藏家和收藏机构也不限于一地。
当故乡成为艺术家真情实感的根基,而非为某种特定他者而设计的自我介绍,格局便不再拘泥。王光乐透过地方习俗触底的是一种可以跨越文化而被感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颜料机械地叠加着,幻化成画布上的生命痕迹,过程,似乎变得比终点更重要。——这种感觉的传导有地域语境的门槛吗?去过或没去过闽北的人,都可以用自己丰沛的想象力、敏锐的感知力与“寿漆”的内核对话,因为本质是在与人人面对的时间和生命对话。事实也是这样,收藏这些作品的人显然不限于闽籍藏家或者中国藏家。即便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那些作为创作起点的地方性,也能从中获得一些熟悉又新鲜的东西。
“木兰溪”是陈彧君早期的一个项目,灵感来自他家乡福建莆田的母亲河。他说木兰溪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东西:“我一直在回归故乡,回到自己的母体文化角度来探讨艺术,它是一种在这个时代做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一个标尺。”最近势象空间正在举办陈彧君的个展“相地通景”(Locality as University),展示了他的一些近作,一些从“木兰溪”出发展开的“南洋想象”。展览文字这样解读他的工作方法:相地与通景,并非时髦的发生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在地性,或是某种被全球化倒逼出的在地意识,而是一种“并列”与“同时”发生的关系。外界抽不走这些中国超当代艺术家血液里的东西,它静静地流淌,随着游子的野心走遍他乡的风景。
陈彧君,《生长/世界地图NO.2100618》,麻布上综合材料,2021,600x330cm
文章来源: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